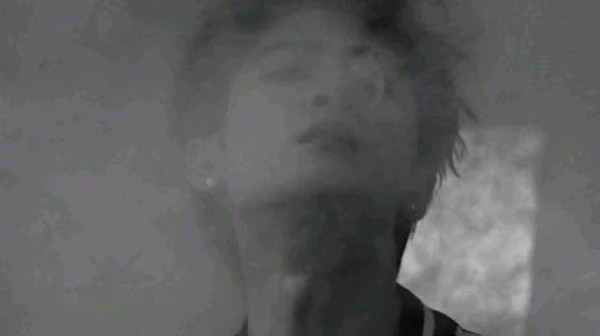性情与理智之争:《安提戈涅》中的悲剧因素
在《安提戈涅》中,有众多值得分析的点,例如神与人,或神法与城邦律令之间的关系,等等。但在我看来,最本质的问题是人的性情和理智间的关系:人有没有可能时刻让理智控制性情?在文中的三位悲剧人物,安提戈涅、克瑞翁和海蒙身上,答案是否定的。安提戈涅的想象力、克瑞翁的顽固、海蒙对爱情的执着和弑父的负罪感,三位人物不同的性情分别剥夺了他们的理性,从而无法理解他人,最后导致了他们的悲剧。
安提戈涅:敬神,想象和诅咒
在剧中,安提戈涅极度敬神。她来对抗克瑞翁所颁布的法律,埋葬波吕涅克斯的第一重理由便是“这是神法的规定”。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安提戈涅会如此敬神?同时令人费解的一点是,安提戈涅这个名字本身有了“禁止生育”的意味,而安提戈涅在生命终了时说未婚而死是自己的诅咒。这突兀的诅咒是什么意思?他们二者又有什么关联?
安提戈涅对神的崇拜最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她充分的想象力和城邦的古老习俗。安提戈涅充分的想象力在戏剧一开头就有所体现。当她描绘波吕涅克斯的尸体时,她说这是给猛禽的“美妙的贮藏品”,这尸体会被“痛快”地食用。这样的描绘不仅不恐怖,还勾起读者对尸体的遐想,这其实是在美化尸体。后来克瑞翁描述尸体时,则说让其被野兽“吞食”,最终“血肉模糊”。这种场面是让人恶心的,但这才是暴尸野外应有的场景。两相比较,安提戈涅富于想象力的特点一目了然。相比现实城邦,虚无缥缈的神界能让其想象力充分施展。因此安提戈涅对神界和神充满幻想和崇拜。第二,神,以及神法象征着古希腊城邦的传统,自然是要遵守的。理论上,如果克瑞翁不是国王,他的提议肯定会被看做背离传统,而被排斥。
安提戈涅对神的尊敬影响了她现实世界的人际关系。安提戈涅认为在家庭关系中,父亲、兄弟姐妹比配偶、儿子等更加重要,因为前者是先天被安排好的,因此更有神圣性,而后者是人可以选择的。所以安提戈涅说,如果死去的不是自己的哥哥而是自己的丈夫或者孩子,那么自己就绝不会违抗克瑞翁。可以推想,对于安提戈涅来说家庭无疑比城邦更加重要,因为家庭的血缘关系是天然的,而城邦中的人际关系都是后天产生的。在剧中,安提戈涅没有和象征城邦居民的歌队长,甚至和自己的丈夫海蒙说过一句话。甚至因为敬神,她看待死亡和死者的方式也和常人不同。对安提戈涅而言,死亡或许意味着在冥界接着生活,意味着她可以再次见到亲爱的父亲和兄长,也意味着她离神更近了一步。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她和伊斯墨涅和克瑞翁争执时,她反复强调死亡对她来说是最好的结果。而对神不那么狂热的伊斯墨涅最后则说“你是热心去做一件寒心的事情”。在她看来,活人和死人的区别是天差地别,一目了然的。
这可以引申出安提戈涅要埋葬波吕涅克斯的另一重原因,便是要洗刷家族的诅咒。俄狄浦斯家族的诅咒从祖父辈开始,体现在俄狄浦斯身上。“弑父娶母”的本质是对“人之为人”标准的违反,现在这个诅咒又出现在了安提戈涅那一代上:波吕涅克斯死后不被埋葬,得不到人作为人应该有的待遇。在《俄狄浦斯王》的结尾,俄狄浦斯担忧自己的诅咒会不会延续到自己的孩子身上。安提戈涅在文中反复强调自己已经受不了这种出现在自己家族中的悲剧,她不想父辈的不光彩重新在自己身上重演,所以她非埋不可。换而言之,如果波不是她兄弟或者她家没有这个诅咒,她未必会有那么积极。不仅如此,她还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是她埋的。在原文中,伊斯摩涅曾劝安提戈涅要埋也要偷偷摸摸地不要被别人发现, 结果被安提戈涅狠狠鄙视:“你要是保持缄默,不向大众宣布,那么我就更加恨你。"这一举措或许可以看成一种对诅咒的回应和对城邦公民的一种回应:父辈和祖辈虽然因为诅咒”做不了人了“,但诅咒不会延续下去,我们这一代依旧是未被诅咒的,可以拥有和其他人一样的待遇,我们的尸体自然也可以被好好安葬。而且不是依靠神力,或者他人的力量,是凭借这个家族成员自己的努力破除了诅咒。
其次,在一个家庭中,死人比活人更加重要,因为死者更接近神,安提戈涅敬神,因此也更加亲近死者。这就是为什么当伊斯墨涅和波吕涅克斯相比较时,安提戈涅毫不留情地斥责伊斯墨涅,但是当伊斯墨涅提出要和安提戈涅一同受罚时,安提戈涅说自己的死亡就足够了,让伊斯墨涅不要死;后来安提戈涅又说当嘲笑伊斯墨涅时,她心中也是苦的。这都说明安提戈涅心中其实是爱伊斯摩涅的,只是相对于让安提戈涅陷入狂热的神法来说,她没有那么重要。
安提戈涅对神的崇拜,不仅仅决定了她看待其他人的方式,也使得她和其他人“不能够好好说话“。极端敬神以及由此导致的一定要埋葬波吕涅克斯的举动和决心,将她和所有人隔绝开来了,甚至因此被抓,成为罪犯。安提戈涅和克瑞翁,甚至伊斯墨涅,都因为是否要埋葬尸体,以及是否要尊重神法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更要命的是,安提戈涅对神的崇拜太过疯狂,以至于她不能理解她人任何不敬神的举动,从而也不可能有任何妥协。面对克瑞翁,即使她证明不出自己那么做的合理性,也依旧抱定一个信念:同是兄弟,也同时死者,波吕涅克斯和将厄忒俄克勒斯就应该受到公平的对待。伊斯墨涅的妥协同样被安提戈涅拒绝,尽管前者是很有道理的。她不是没有考虑神的要素,而是考虑到自己在力量和权威上都无法和克瑞翁抗衡这一事实。站在常人的角度,这才是合理的。安提戈涅对于伊斯墨涅最后的提出的“偷偷埋葬”的说法不屑一顾,足以证明安在敬神这件事上已然进入了一个极端。
但同时,虽然安提戈涅主动将自己和他人对立了起来,他人和她的关联却更加紧密了。伊斯墨涅最初态度随意,说“你要去就去吧“,现在却愿意和她一起死:作为她的亲人之一,她同样认为安提戈涅是可爱的;虽然她和城邦中的公民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是整个城邦此时都在讨论她,“只有她最不应当这样最悲惨的死去!”;她的未婚夫海蒙也来向克瑞翁求情。无论是家庭成员还是城邦居民,和她的联系此时都变得比以往紧密。换一个角度想,安提戈涅所谓的“洗刷诅咒”本质上是要城邦居民对她家族的偏见,重新认可他们,因而配得上人死后应该被埋葬的待遇,而不是在神灵面前证明自己的家族未被诅咒,不然的话她其实没有埋葬的必要。她所谓的赢得神的“荣耀”,在城邦公民口中就是“黄金似地光荣”,也就是世俗世界的荣耀。她虽然主观上将伊斯墨涅等人区分了开来,但是客观上她的一举一动都以人与人的相互关联作为基础,这种关系甚至扩大到了同死人的关联。
因此,其实不论让安提戈涅或者还是死去,她和众人都不会彻底割裂。但最终,她受到的刑罚是被关在一个洞穴中,让她“既不是住在人世,也不是住在冥界,既不是同活人在一起,也不是同死人在一起”。这个刑罚的本质意义在于,她切断了安提戈涅和所有人——不管是活人如伊斯墨涅,还是死人如波吕涅克斯——之间的关系纽带。她在受刑中反复强调的,便是自己的孤独,“孤孤单单,无亲无友”。这才是最悲惨的地方。至于所谓的和神共享荣耀,未必是安提戈涅真正想要的。临行前歌队长对她说她“生前和死时都与天神同命”此时,安提戈涅却说这是在讥笑她。如果她真的在乎神的荣耀,不应该这样反应。我们可以推想,安提戈涅敬神的本质目的不是神本身,而是神,甚至由此引发出冥界和死者可以满足自己的想象力,和而不是真的崇拜神。
但是,安提戈涅能不能和人建立关联呢?不能,因为她被诅咒了。诅咒的内容是“她没有结婚和生育就会死”。结婚所代表的是和另一个人建立联系,而生育则是孕育一个新生命。这两件事都是建立人与人关系的第一步,也是最简单的一步。配偶关系之上就是家庭,而后才是整个城邦。这两件事安提戈涅都做不了,也就寓示着她无法从根本上建立人和人的关系。她大力地颂扬自己和父亲以及兄长间关系的神圣性,对配偶和儿女的态度却有轻慢。但不正是配偶和生育创造出了父女关系和兄弟关系么?
因此,安提戈涅直到死都没能成婚,可以理解成她始终没能真正地理解哪怕一个人。虽然她有未婚夫海蒙,但是整部剧中二人没有一句对话。海蒙深深地爱着安提戈涅,但是安提戈涅对于海蒙又有多少了解呢?对于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几乎只有激烈的争吵。她直到临死才对这件事懊悔,说明她对人与人的关系只有最模糊的认识,也就是生和死的区别。只有当一个人要死了,她会本能地期望他人不要死,就像她对伊斯墨涅表现出来的那样。这或许也就是她爱别人的全部表现了。除此以外,她无法再进一步的理解他人。这或许是由于诅咒剥夺了她这么做的能力;也或许是因为她爱想象的性情让她没有办法理智地思考这个世界,而理性是理解现实世界的基础。死者的世界是没有逻辑可言的,安提戈涅可以尽情想象,因而可以尽情喜爱;但现实世界中,想要理解他人,就要权衡各种要素。如果安提戈涅想理解伊斯墨涅,她就必须像伊斯墨涅一样权衡力量、地位和神法,而这意味着抑制安提戈涅的想象力。安提戈涅当然做不到这一点。她生来是跟着别人爱,但是却不知道怎么爱。这便是安提戈涅的悲剧。她看似对神法毫无来由的崇敬背后,充斥着她的想象力,让她理解不了他人,最终酿成自己的死亡,这引发了之后一系列其他悲剧。
克瑞翁:顽固和自私
和安提戈涅一样,克瑞翁在剧中同样很不通情达理,当他的亲儿子海蒙要殉情的时候,他还傻傻地问:“孩子你要做什么?”他不通达清理的理由是和安提戈涅不同。安提戈涅是出于想象的性情,而克瑞翁则是顽固和自私的性情。
克瑞翁自私的性情在《俄狄浦斯王》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在《俄狄浦斯王》中,当俄狄浦斯质疑克瑞翁要夺权时,他反驳的理由是:君王的一切好处自己都能够享受到,但是自己却不需要承担君王需要承担的责任,所以自己有什么理由要夺权呢?从这一段对话中不仅可以看出克瑞翁自私的性情,也可以看出克瑞翁因何物自私:安逸和享受,也可以看出克瑞翁看待问题的方式:他只比较一样事物为自己带来的利弊。如果利大于弊,他就采用,如果弊大于利,他就放弃。当时在他看来,王位带来的弊端大于好处,所以他就放弃了。但他不会思考王位自身象征着什么。他的关注点和思考方式在《安提戈涅》中一脉相承。
只有自私且贪图安逸的人,才会如此迫不及待的划分敌友。划分敌友的标准也很简单:对自己不利就是敌人,有利就是朋友。克瑞翁对城邦公民讲述的第一段话中,就称厄忒俄克勒斯为城邦的英雄,波吕涅克斯为城邦的叛徒,并下令埋葬英雄,将叛徒暴尸荒野,同时将城邦的首要目标定位“安全”,其他都是次要。可以想见,波吕涅克斯影响到了克瑞翁的安全,而厄忒俄克勒斯保护了他的安全。对自己有利的人当然要大加奖赏,对自己不利则要重重打击,这是克瑞翁的逻辑。问题是,是否有其他看待这场战争的逻辑?即使没有,是否有其他处理波吕尼刻斯尸体的方法?
第一个问题涉及到厄忒俄克勒斯和波吕涅克斯的长幼之争,在最初的古希腊文本中,克瑞翁讲述波吕涅克斯的身份用的是“ξύναιμον”一词,意为“血亲”,也就是说,但从这个文本中我们无法得知波吕尼刻斯到底是不是长子。在索福克勒斯后来创作的《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波吕涅克斯亲口说自己是长子,而厄忒俄克勒斯是次子。如果长幼关系的确是这样,那么忒拜城战争的实质并不是守护城邦之争,而是争夺王位之争。波吕涅克斯身为长子,有王位的合法继承权,厄忒俄克勒斯没有,却将波吕涅克斯逐出忒拜城,导致两人甚至是两国的战争。这样看来,克瑞翁看待这件事的角度即使依旧成立,也不是唯一的了。其次,就算波和厄的关系如克瑞翁所说,处理波的尸体的方法也绝不止暴尸荒野这一种,尤其是有人明确反对这种处理的前提下。如果克瑞翁是一名良好的统治者,就应该考虑到他人的情绪,妥善地处理好波吕涅克斯“叛国”的身份和“原先城邦的居民”这两重身份。
但克瑞翁不仅粗疏武断地断定了两人的身份,也粗暴地处理了波吕涅克斯的尸体。同时,他利用国王的身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整个城邦公民。当他宣布完自己的措施之后,歌队长的回复耐人寻味:他并没有明确地拥护或者反对,而是说这项决定很合乎克瑞翁自己的意思,又说他有权利用任何法令约束死者和活人。可以想见,城邦公民不是完全同意他的意见,而是正像安提戈涅后来指出的,碍于他的权力不得不听从。
克瑞翁的自大一方面由于其自私到了极点,希望所有事物都合他的心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用血亲关系取得了王位。原先在王族中,他就是长辈,进行着家长式的统治。前文已经说过,伦理关系有神圣性,而克瑞翁因为血亲继承王位,自然而然地将原来家长式的权威带到了城邦治理中。国王的权力大到让他不去理会他人的想法,可以只顾自己的私利;就像安提戈涅以神法为借口,满足自己的想象,不关注他人的想法一样。从这个角度,我们便能够理解安提戈涅和克瑞翁那场突兀且激烈的对话。一方以神法为借口,另一方王权和法律为借口,但其实安提戈涅诉说自己的臆想,例如“谁知道下界鬼魂会不会认为这是无可告罪的?”,克瑞翁诉说自己极端的自私“仇人绝不会成为朋友,死后也不会”。他们谁都没有和城邦公民进行过讨论,因此谁都不代表公众的意见。只是一方的论断恰好有战争的表象作为依据,另一方又恰好有传统神法作为依据。
克瑞翁如此关注自己的安逸,其他人和事在他眼中就只是实现安全的工具,对敌友的划分就是如此。他也不再考虑其他事物自身的内涵,其他人的想法。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他对神,以及神圣性的态度。如前文所说,克瑞翁作为王族的长辈,其权力天生带有神圣性。但是他只是利用这一点提出自己的个人观点。在开篇的对话中,他说到:“请无所不能的宙斯见证”。他试图用神来让自己的观点合法化,而并不思考传统神法的意义。同样在戏剧的末尾,当先知告诉克瑞翁神灵反对他的命令时,他才真正地感到害怕,因为他的统治权威被真正撼动了。但就算在此时,他也没有思考神法和他的命令之间到底哪里有矛盾,而是简单地遵从神律,修改法令。在统治过程中同样如此,他运用“品德”,“明智”等词汇,但是他并不思考这些词的含义是什么,自己的法令到底能否体现这些原则。他只是用这些宏大深刻的词汇述说自己简陋狭隘的思想。
克瑞翁对众人更加不会将心比心。面对安提戈涅有关命运、死亡和血亲的,充满激情的述说,Creon只是回应道:“太顽强地意志容易受到挫折。”他只在乎这些事情能不能保证安全,而不去思考这段话中的深意。其后他的话语中运用“女人”、“奴隶”等字眼同是如此,这些标签附在安提戈涅身上,她就无法再妨碍自己的统治;当歌队小心翼翼地提出埋葬可能暗含神意时,他粗暴地回绝他们,并将城邦中的反对意见理解为有人故意实施阴谋,破坏城邦,从而影响其统治的阴谋。当伊斯墨涅以海蒙的婚姻为理由想免除安提戈涅的死亡时,他更是直言不讳地说到:“有其他的土地让他耕种。”他根本不正视海蒙的婚事,换而言之,他不理解儿子。当海蒙劝说克瑞翁时,克瑞翁彻底暴露了自己的想法,“难道我要按照别人的意思,而不是自己的意思统治国王吗?”国王将国家看作私事,不论这是不是习俗,都是不对的。城邦统治涉及公众,绝不是一个人的私事。这暴露出他缺乏政治统治的基本素质,也是酿成悲剧的要素。
克瑞翁开始理解他人是以他儿子和妻子的死亡为代价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是“顽固性情惹出的祸事”。克瑞翁的错误就是他顽固的性情让他不再谨慎。他一再坚持自己的观点,并用统治者的身份强迫整个城邦接受,而不在乎他人的感受。直到自己的顽固引起了儿子和妻子的死亡,他才深切地体会到自己所追求的安逸生活不建立在强力的法令和敌我划分之上,而是建立在人和人的纽带之上。他最后在悲伤中理解了何为正义。正义并不建立在一个狭隘的价值判断上,而是一定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感受。也正因如此,统治者在论断的时候不应狂妄,而要谨慎,要考虑到尽可能多的人的想法。
克瑞翁和安提戈涅的悲剧都是由于他们的性情压制住了他们的理性。但是这是他们的“错”,还是人性中不可避免的悲剧因素?很可能是后者。即使是一贯保持理性的人,也可能被性情控制不能自已。这一点就表现在海蒙身上。
海蒙:从理智到性情的转变
海蒙是全剧中最通情达理的人物之一。他在劝说父亲时,对父亲的身份表现出了足够的尊重,说到“不会把婚姻看得比父亲的善良教导更重”。同时又十分委婉地道出了克瑞翁应该考虑城邦中很大一部分人的观点。海蒙也是全剧中除了歌队长以外唯一一个不是从个人性情,如克瑞翁和安提戈涅,或者从现实需要,如伊斯墨涅,而是听取民意,从公众立场判断是否要埋葬波吕涅克斯的人。在被克瑞翁拒绝后,他点出城邦事物是公事,不能一人独断。否则就和“在沙漠中统治”无异。但是,当克瑞翁误认为海蒙做的一切都是处于对安提戈涅的爱,甚至威胁要在海蒙面前处死她的时候,海蒙明显不再能够保持理性,说到自己会为了安提戈涅殉情。很明显此时海蒙的关注点从整个城邦变成了安提戈涅,他的身份也从一位大臣或者海蒙的儿子,变成了安提戈涅的未婚夫。他思考问题的角度也从离心变成了悲剧。当安提戈涅的死的时候,海蒙便彻底丧失了理智,连他的眼睛都是“凶恶”的了。此时他表现出的恶完全是由于克瑞翁夺走了自己至爱之人的性命。随后他砍向父亲未成功,又有了弑父的负罪感,便自杀,死前将安提戈涅抱入怀中。让他自杀的两重要素是对安提戈涅的爱情和违背伦理的内疚之情。但即使在后者中,他想到的只是作为概念的“父亲”和冷冰冰的道德约束,而不是他的父亲克瑞翁。死守教条正是失去理智的表现。因这一规则而自杀,其背后的逻辑正如安提戈涅因神法选择埋葬尸体,克瑞翁选择不埋葬一样。如果海蒙和之前一样有理性,就应该知道克瑞翁并不想让他死。但即使他明白这点,对安提戈涅的爱依旧很可能压过这一理性,让他殉情。海蒙从头到尾表现出的是从理性走向性情的过程。这一过程因死亡引起,几乎不可能让人保持理智。就像波吕尼刻斯的死引动安提戈涅,安提戈涅引动海蒙,海蒙动欧律狄克,欧律狄克引动克瑞翁一样。
总结:
作者在剧中暗含的问题就是:我们能否保持自身的理性,而不被性情控制?在安提戈涅,克瑞翁和海蒙身上,答案是否定的。实上总有事物可以激起我们的性情,超过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在安提戈涅身上,这是对神和神法的幻想;在克瑞翁身上,这是由自私和顽固引起的自大;对于海蒙来说,则是爱情;对于欧律狄克来说,是亲情。但是我们每个人的性情想要显露,都需要以人和人的联系作为基础。没有了他人,我们的性情便无处发泄,但是要和他者沟通,我们就要压制住自己的性情,用理性理解他人,这样才能懂得他人看问题的思路。每一个人的情感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逻辑和理性是相互通达的。人与人的联系在我们的生活中太普遍,我们会将它视作理所当然的存在,因为也就不会重视它。生育是这种联系的起点,而死亡是这种联系的最终剥除。只有当他人死去,我们才会认识到自己生活中的快乐都是由他人乃至人与人的联结带来的。安提戈涅的诅咒“无法生育和结婚就死亡”,本质的结果就是她很难理解他人。只有当死亡来临时,她才能模糊地感到这种关系会被剥除。克瑞翁直到悲剧酿成后才明白这个道理,后悔自己的顽固性情毁掉了自己最亲近和重要人。而海蒙体现出了面对死亡,一个人的理性会如何被性情控制,酿成自己的悲剧。正因如此,歌剧的最后唱到:“谨慎的人最有福”:因为谨慎的人最能够用理性和明智来控制自己情感,同时能够理解他人的情感,因此最能够维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可能是本剧最深刻和本质的内容,不论跨越多久的时空,都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安提戈涅》中暗含的性情和理性的矛盾关系警戒着后人,也引发后人的思考。
参考书目:《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在克罗诺斯》, 《罗先生全集》(增订典藏版) 文景 人名出版社
阅读涉及书籍:《Antigone》,Sophocles I_ The Complete Greek - David Grene
网址:性情与理智之争:《安提戈涅》中的悲剧因素 https://m.mxgxt.com/news/view/1751105
相关内容
安提戈涅人物关系悲剧家中第一人是谁?写了多少戏剧?最著名的是哪个?
杨靖丨《奥涅金》翻译之争
【讲座回顾】丁尔苏|悲剧与现代性:两种虚假的因果关系
华南首演!图米纳斯全新力作《战争与和平》再现俄式戏剧之美
《卡拉马佐夫兄弟》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文学|最后的告别:有关爱与悲伤、失忆与幽默、温馨与智慧
历史的涅槃:印尼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之变迁
安东尼·戈登的职业生涯轨迹:薪资争议、转会风波与私人生活
俄罗斯话剧《叶甫盖尼·奥涅金》将再度来华巡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