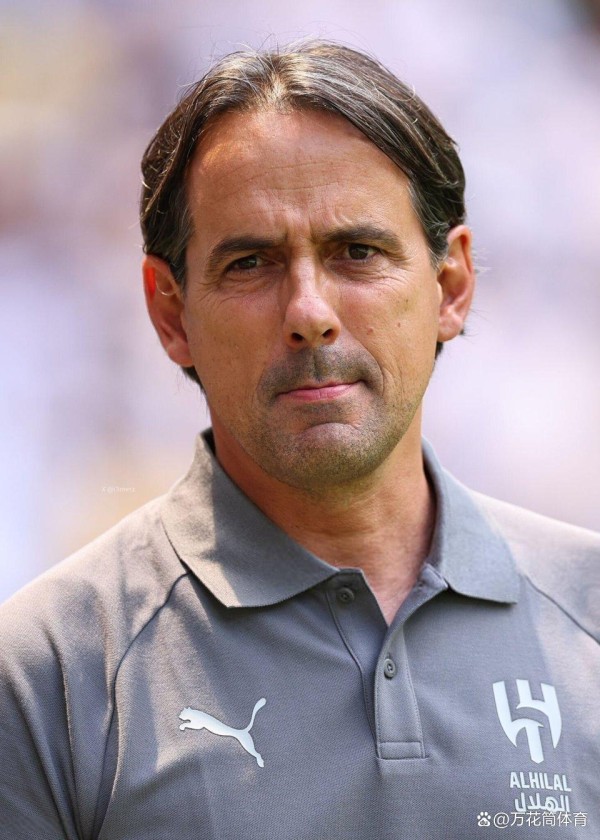接续传统与“多样性”传承
国家艺术基金项目“晋陕蒙冀四省区原生态民歌人才培养”,作为近年来国内规模较大的跨区域民歌人才培训项目,从策划设计,到集中授课、随团实践、采风交流,最后呈现《新时代民歌传承人》的汇报演出,紧凑高效。其学员来自基层演出团体,授课教师包括国内外的演员、导演、教师、学者,整体设计思路显然是努力集合多种优质资源服务演出第一线,体现出山西文艺界一贯踏实务实的作风。中国民歌文化有着数千年的传承积淀,历史上士农工商各阶层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贡献。在当代同样需要也应该需要有更多的人以不同的形式和方式参与探索民歌的传承和发展,“晋陕蒙冀四省区原生态民歌人才培养”无疑在这个方面做了非常重要和有效的努力。从汇报演出看,曲目展示以原生态民歌为主体,适当加入“类民歌”的新创作品,反映出其对当代民歌传承与发展的意愿与态度。舞美配合恰到好处。在当下“舞美成灾”的时代,能够坚持音乐主体性亦属不易。座无虚席的观众,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可以肯定民歌并没有失去“人心”。
这个项目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新时代的民歌应该怎样传承与发展?笔者认为核心在于:接续传统,“多样性”传承。以山西的“原生态”民歌为例,充斥于媒体的基本印象是:表达主题以爱情为主,音色高亢、响亮,演唱“土得掉渣”“基本靠吼”。而提及山西文化就是“山药蛋文化”“走西口文化”。这样一种非常狭隘的认知,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并不断被强化。问题在于,山西民歌有没有其他主题?演唱风格是否只有高、亮、响?演唱标准是否只是基于技巧?凡此种种,应当反思。民歌蕴含丰富,简单以号子、山歌、小调来类分,其风格和内容都极具多样性,这是一种宝贵传统,而非在当代的新变化。
山西作为中国北方历史地理文化的主体之一,历来都是重要的文化中心,其“时髦”特质常常引领潮流。这些文化信息不仅留存于“寺庙”“大院”等古建之中,也大量保留在传统音乐,尤其是民歌之中。今天大众熟知的山西民歌,大多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被挖掘整理,推向舞台,广泛传唱,进而被经典化的。但是,这些曲目是否代表了山西民歌的全部?山西民歌中有没有另外一种或多种风格的曲目存在?例如早在1953年音乐学界对河曲民歌就已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收集曲调400余首,歌词4500余首,限于当时条件,最终出版的《河曲民歌采访专集》中只集中呈现了23首。今天,当我们极尽所能在《走西口》上发挥想象的时候,却忘记了还有更多的民歌沉睡在资料馆里。我们可以对经典民歌进行深加工、再创作,但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还有更大一批民歌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被人们遗忘,甚至根本未被留意。如果说,所谓“民歌发展”首先要继承传统,那么,仅就曲目数量层面的多样性,我们又继承了多少?
当下的民歌演唱,无论是民族唱法,还是“原生态”,“高亮响,柔甜美”已蔚然成风,同时,将音色与区域简单地对等,诸如“晋陕民歌高亢”之类的断语又失于狭隘,加之现代传媒一再强化,审美定式下“原生态”被裁剪,成为一种民歌“快餐”。快餐文化的本质是标准化、浅尝化、庸俗化。由此必然促使民歌演唱风格趋同,演唱者歌唱能力退化。问题在于,歌唱应该是内容先行,还是技巧先行?试问蕴含数千年民族文化的中国民歌中那些浅吟低唱如何“高亮响”?那些忧苦愁绪如何“柔美甜”?一群协同劳作的染坊工人何以能潇洒自如地“高亮响”?原生态民歌舞台化,必然带来艺术加工和二度创作,但是情绪的表达除了舞美的渲染,是否更应该取向于歌唱本身?歌唱者追求技巧精进,尤其是吸收中西所长,追求特性音色,训练自如运腔,无可厚非。但这同样意味着要更加注意“多样性”。例如在“高亮响”之外是否还有基于不同情绪表达而出现的音色处理方式?这一点既是歌唱之常理,也是民歌之事实,为何当前舞台呈现给观众的却只有“冰山一角”,且总是同“一角”。民歌来自民众,演唱者有选择不同歌唱方式的权利,民歌有多种演绎的可能,不能够也不应该将原生态民歌搞成“千人一面”“千人一声”。
民歌最大的动力在于创造,民歌手最大的魅力在于创作。这种创作不同于当下主流音乐教育机制中的专业作曲,而是一种极为宽泛的自由创作,是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积淀下的“信马由缰”“恣意妄为”。这种“恣意妄为”集合了民歌手前人的、同人的、自己的智慧,是民歌生生不息、源源不断的原动力。回顾活跃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一辈歌手,虽目不识丁,基本都是见山唱山,见水唱水,见人唱人,见事唱事,想啥唱啥,现编现唱,越唱越活,越活越强。从当下的现状看,民歌手的这种能力几乎丧失殆尽,只会演唱、拾人牙慧者越来越多,自成一体、唱作俱佳者越来越少。这一问题与当前民歌评价的单一化标准直接相关。在起主导作用的传媒语境下,各种民歌赛事和展演活动对民歌手的评价只重歌唱技巧。事实上,在民歌手依赖的原生环境中,民众对其评价是多样的,除了嗓音好坏、技巧优劣之外,更多的还有曲目多寡、即兴与否等标准。这种标准是中国传统音乐自古即有的,古时乐人“斗曲”不仅比技艺高低,更比谁更善“新声”,这种传统至今犹存,如西北“花儿会”、西南“歌圩节”等各地区民族歌会中的“斗歌”“对歌”,都以掌握曲目多者为尊。借用晋陕地区评价“伞头”歌者的话,“会两三首不算本事,唱的多,编的巧,才是能耐”。标准的多样性,是民歌在深层次上继承和发扬传统的一条正路。
民歌需要发展,但不必急于标新立异。传统不是包袱,而是指路明灯。我们可以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扩大传播层面,可以借助各种流行艺术拓展受众市场。但民歌之所以为“民歌”,之所以被视作众多艺术形式的母体,核心价值在于其背后的数千年文化积淀,在其对传统的接续,而绝非其他。传统,是民歌的独特性之根本。我们对民歌的传统,尤其是“多样性”方面,认识远远不够,应该首先踏实认真做功课。对于民歌传统的“多样性”传承至少应包括:由历史信息、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探索而引发曲目内容的多样性传承;由曲目内容的多样性探索而引发的表现方式与手段的多样性传承;由表现方式与手段的多样性探索而引发的技术与风格的多样性传承,以及基于多种层面的挖掘而引发的创作方式、传播途径的多样性探索。
参天大树必有深根沃土。在民歌发展的道路上,对于音乐创作与表现形式的努力,是一种创新;对于传统的多层面的挖掘、重建,更是一种创新,而且是一种更有根脉、更具深度、更加高级的创新。
网址:接续传统与“多样性”传承 https://m.mxgxt.com/news/view/1910457
相关内容
摩梭传统音乐传承人:将传统音乐传承下去多元文化传承视域下传统音乐的创新
传承传统文化新师徒关系是武术传承之根
中国传统音乐在节日中的传承与创新.docx
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与创新遵循哪些原则
传统武术最主要的传承方式——师徒传承
开拓多元文化视角 推进传统音乐文化传承创新
沈阳相声:在传统与潮流的碰撞中传承“笑声”
地域性非遗音乐文化的“多维”传承
传统武术的基本传承方式——师徒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