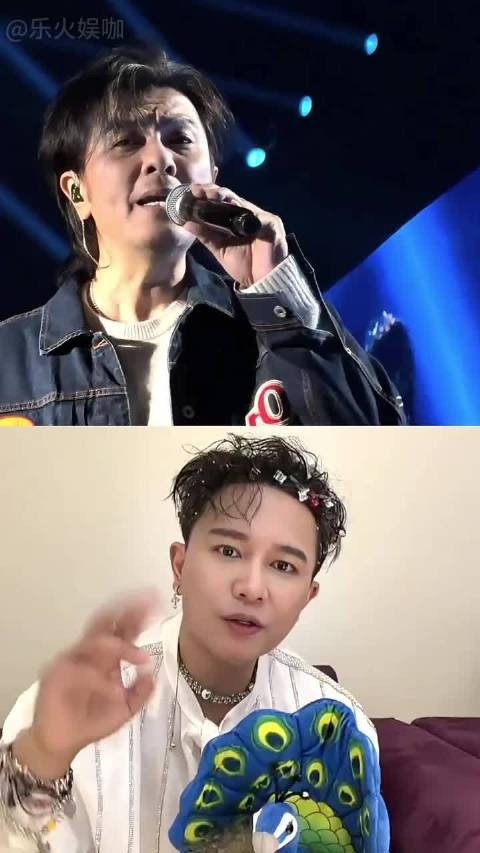永不消逝的明星:《被遗忘的时光》之后的迪伦
第七章 永不消逝的明星:《被遗忘的时光》之后的迪伦
1997年是迪伦职业生涯最重要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同时发生了两件事情,彻底改变了迪伦明星身份的含义。一件是他的住院,另一件是《被遗忘的时光》的发行。我在第一章中提到,虽然文学评论家可能会反对对歌曲的传记式解读,但实际上,明星身份是赋予歌曲含义的主要形式,尽管明星身份与传记密切相关,但明星身份并不依赖于传记的准确程度。对此,《被遗忘的时光》的发行,就是再好不过的说明了。事实上,迪伦生病与《被遗忘的时光》并无关联——专辑中的歌曲写于1996年末,并于1997年一二月间完成录制,而直到5月份,迪伦才病倒住院。但若依据明星身份,这两件事便是紧密相连的。生病这件事,促成了对迪伦的理解,为人们接受和解读专辑中的歌曲提供了情境。专辑一发行,上面的歌曲更是强化了公众的印象。
《被遗忘的时光》在世界范围内都广受赞誉。可想而知,它得到的评价自然高于迪伦的其他专辑。在我看来,这些极高的评价并非歌词创作之功,也不仅仅是为他幸存于世而流露出的欣慰之情。这张专辑之所以能大获成功,主要是因为它呈现出一种始终如一而连贯的音乐风格,与迪伦的当代明星形象相协调。这主要体现在声音上,不过专辑的风格(闷热而封闭的)与歌词也都有所反映。迈克尔·格雷对专辑的主题做了很好的归纳:
无穷无尽,近乎强迫症地不停行走,孤立无援,缺少与他人接触的意识;令人窒息的空虚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毫无目的的生活;时而有对死亡的渴望,时而又希望时间没有流逝殆尽;确信在很久以前自己曾步入歧途,其中之一便是错失真爱;确信别无他话可说,说出来也毫无意义;心神疲惫,夹杂着对所有失去之物的极度悲痛。1
我想对此做进一步的综合分析,解释在九十年代早期,与迪伦的特定明星形象相联系的三大主题。第一个是强调持续运动,尤其是行走。很多歌曲都在开头提到行走(“我正走在一条死去的街道上”,“将要走上那条泥土路”,“我在夏夜里尽情漫步”……)。正如格雷指出的,这种行走似乎是无法避免的,或者说,是强制性的。这自然与NET创造出的迪伦概念相关。“短暂”这一持续“运动”的概念,是摇滚文化的一个主要元素,而迪伦也一直被视为是一个躁动不安的人。然而,从NET举办伊始,这种躁动不安便被赋予了一个人体形象——巡游的民谣歌手,四处漂泊的流浪汉,总在前往下一个声色场所,暂时地歇脚,也在一场演出完成时便告结束,然后继续前进。因而,迪伦的当代形象也处于持续变动的状态,总在向下一场演出进发。1997年,记者艾伦·杰克逊写道:“这是一个只存在于聚光灯下的男人。他每晚在世界某处的舞台上重获新生,但除此之外,便永远都是一个居无定所的流浪汉,心甘情愿成为永不停止的巡演的奴隶。”当《被遗忘的时光》提及持续的、强制性的行走时,上述形象更是得到了强化。
《被遗忘的时光》的第二个主题就是无话可说。整张专辑一再提到,无法准确说出想表达的意思:
感觉似乎在和谁说话,但我不知道究竟是谁
(《一百万里》)
现在你可以把这本书密封起来,再也不去写它了
(《设法上天堂》)
我厌倦了说话,厌倦了设法解释
(《直到我爱上你》)
这显然与九十年代迪伦的形象有关——致力于表演,而非创作。在这段时期,迪伦多次做出声明,说“这个世界已不再需要更多的歌曲”,两张翻唱专辑,《像我那样对你好》和《错乱世界》的发行,更是印证了这一说法(2004年,他声称“如果我是为自己创造音乐,那我只会翻唱查理·帕顿的老歌”)。然而,正如之前所提到的,许多乐评人和粉丝并不愿放弃迪伦是一个词作者的观念,对他转向表演的行为也多有指摘。因此,颇为讽刺的是,迪伦关于不需要新歌词的言论,只有在他成功创作出新歌时,才会引起听众的重视,而这恰恰表明,迪伦永远都无法彻底改变他的明星形象。但无论成功与否,《高地情歌》中关于“要说的话越来越少”的声明,都与九十年代鲍勃·迪伦的形象完全相符。
《被遗忘的时光》的最后一个主题是衰老和死亡。逝去的青春,衰退的身体,即将降临的隐喻式黑暗,都贯穿于整张专辑。这是评论家们理解最透彻的一个主题,也与他的生平传记有着最明显的关联。正是在这一主题下,明星形象与专辑引起的反响实现了直接的融合。媒体很快便把迪伦住院的那段时间,与这张专辑预示灭亡的特征联系起来。一些媒体还妄下结论,认为疾病是忧郁专辑产生的必然原因。其他媒体虽观点相异,但仍笃定,迪伦肯定事先有所预见。甚至是那些明确指出与传记相矛盾的评论,也公然地把两件事紧密挂钩。
《被遗忘的时光》之所以大受欢迎,关键就在于它呈现出一个连贯一致的歌手形象,与明星迪伦的公众概念相吻合。这点可从歌词里看出一二——这张专辑在主题上具有一致性——但到目前为止,其中最重要的元素还是声音。歌曲从声音中所得的含义,要超过从歌词语义中所得的含义。这一点在这张专辑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就《被遗忘的时光》来说,迪伦的声音体现了这张专辑的重要主题。它听起来像是一个年老者的声音,非常老,远比迪伦本人要老得多,毫无疑问,这个声音震惊了许多听众:
他在《被遗忘的时光》中发出的邪恶的、有如生锈的消音器般的咆哮声……震惊了全世界,因为它与昔日的辉煌格格不入——完全是一个新事物。2
这一全新的歌声最初出现在《像我那样对你好》《错乱世界》和《不插电》中,但很少有人听过这些唱片。《被遗忘的时光》是迪伦最成功的唱片之一,成为继《慢车开来》后,他第一张销售破百万的唱片。大部分购买这张专辑的人,至少在《哦,仁慈》,或是《异教徒》之后,或是更早之前,就再没听过迪伦演唱了。可以说,《被遗忘的时光》中的声音,与鲍勃·迪伦原来的声音毫不相符。[1]
年龄的变化自然是部分原因,但毫无疑问,迪伦的声音还受到了NET的影响(当录制这张专辑时,他已经举行了749场NET的演出)。由于声带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从1997年起,声带就已经愈加压缩了),迪伦的声音显得沙哑、粗犷而低沉。对于他最近的专辑,有评论称他的嗓音“极其沙哑”,是一种“沙沙的,似乎伤痕累累的咆哮”,和一种“极不清楚、极其刺耳的刮擦声,仿佛有鲜血从迪伦的喉咙中迸出”。这个声音就像是玛士撒拉式老人的声音那样苍老。但这个声音又具有惊人的“现在时”特征,它充满了丰富的织体,几乎给人一种触感。威廉姆斯认为,听《被遗忘的时光》,就像是坐在演唱会的前几排,3而这种效果正源于那发自肺腑的声音。当然,这个声音夹杂着一种纹理,一种浓密的纹理,富有自然的庄重与美丽:400年橡树的纹理,在咆哮声中熊熊燃烧。
在我看来,继《被遗忘的时光》发行后,迪伦的明星形象如何发展,受到了声音的“年龄”的重大影响(后面我会对此做具体论述)。根据一般的理解,某人的声音可以揭示其真实性格。正如弗里斯指出的,“我们假定自己可以从某人的声音中洞悉其生活——而这种生活不会受歌手的技巧所影响”。4如今,迪伦被看作是一个老人,而非中年人(对摇滚音乐来说,这或许更像是个有问题的标签)——当《红色天空下》发行时,他49岁,而当《被遗忘的时光》发行时,他已经56岁,越来越接近70岁了。这时,年龄已经不再是一种内在的优势。可以对这一年龄做不同的解读,比如,象征衰老和破败。但在这里,迪伦的年龄则代表着智慧和刚毅。同样,这又是由声音造成的印象——在《被遗忘的时光》中,歌手表达了一种疏离、孤寂,以及与世界的隔离之感,但同时又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内在人格。乐天知命,即是力量。歌手无须过多借助于自己所说的内容,而只要以权威的方式去陈述,便可守住自己的内在优势。迪伦“诚实地表示,自己已经丧失了全部的真实性”。5在年龄面前,这种品质,这种尊严和反抗精神,正是NET的重要特征,也基本上是迪伦1997年之后明星身份的重要特征。
《被遗忘的时光》发行之后,迪伦受到了铺天盖地的赞美,而这是继六十年代以后从未有过的。在1997年到2001年之间,他频获嘉奖:多萝西/丽莲·吉许荣誉奖;肯尼迪中心荣誉终身成就奖;《被遗忘的时光》三次获得格莱美奖,其中包括他首个格莱美大奖(年度专辑);保拉音乐奖;金球奖;以及他个人十分满意的奥斯卡奖。而且在这些年里,他每年都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他在1997年之后的作品——专辑《被遗忘的时光》《“爱与窃”》和《摩登时代》,自传《鲍勃·迪伦回忆录》,以及纪录片《迷途之家》——更是好评如潮。《“爱与窃”》成为九年来第一张被《滚石》评为五星的专辑。他的商业地位同样大大提高——三张专辑在全世界都进入榜单前十,而《摩登时代》更是成为1976年后迪伦首张美国排名第一的专辑。
尽管迪伦试图将自己重新定位成一个表演者,而非词作者,但显然很讽刺的是,只有在发布新歌专辑时,他才会重新获得好评。尽管迪伦试图通过NET来重新调整他的明星形象,但在人们心中,他依然是同时代最伟大的词作者。这也表明,原创具有更广泛的文化理想化色彩。然而,这又使讽刺意味加倍,因为从传统意义上来说,迪伦在1997年所发行的专辑并非“原创”。恰恰相反,那张专辑对早期音乐素材做了精心的叠加和整合,是对蓝调、民谣和流行演奏中的线条与图像的拼接。第一首歌叫作《思念成疾》,是对汉克·威廉姆斯的热门歌曲《相思布鲁斯》的缅怀,第二首歌《泥土路上的布鲁斯》,则模仿了查理·巴顿的《行走在泥土路上的布鲁斯》。《站在门口》中的歌词“抽一支廉价的香烟”,摘自吉米·罗杰斯的《等待火车》。在歌曲《高地情歌》中,迪伦把云朵比作“微微振荡的战车”,等等。专辑还有对其他音乐的引用:《让你感受我的爱》的旋律来自《你属于我》,而《站在门口》的起始音符,会让人想起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金曲《坠入爱河》。[2]这种作曲方式一直延续到迪伦后来的作品,《一切已改变》中“我是一个满脑忧虑的男人”这句歌词,在之前的很多蓝调歌曲中都出现过,其中《四十英里崎岖路》是杜安·艾迪的主打歌曲;《“爱与窃”》中的歌词“我相信我会拂去扫帚上的尘埃”出自《滚滚洪流》,一首普通蓝调歌曲的名称,而查理·巴顿还曾录制了一首叫作《到处滚滚洪流》的歌曲;《胖子双胞胎兄弟》中的“我把爱全给你,却又被丢弃”,则复制了罗伯特·约翰逊《徒劳的爱》中的歌词;《甜心宝贝》的最后一句歌词,“抬头看,抬头看——寻找你的造物主——因为加百利已经吹响了号角”,其实来自弗兰克·辛纳特拉的《寂寞之路》。当人们发现,迪伦引用日本作者佐贺纯一的小说《浅草博徒一代》里的文字,却未标明出处,媒体顿时一片哗然。[3]这种引用方式激起了众多评论员的议论。一般人认为,这是对传统观念下著作权的破坏。6对其他歌曲中歌词的引用,既强化了《被遗忘的时光》的中心主题——要说的话越来越少,也凸显了迪伦之前的一个观点——“早已被人做过/早已被记载在了书中”(《太多微不足道的事》)。[4]不过,在本章,我想从稍有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思考引文的使用,如何影响对音乐的时间性体验,它们如何把迪伦与“传统”联系起来,以及这种双重过程如何影响迪伦的明星形象。在我看来,正是从时间和传统的关系中,我们可以找到迪伦得以东山再起的原因。
网址:永不消逝的明星:《被遗忘的时光》之后的迪伦 https://m.mxgxt.com/news/view/1894131
相关内容
被众明星青睐的歌曲《被遗忘的时光》,都有谁宠爱过?被遗忘的时光原唱是谁,介绍这首经典歌曲背后的故事
夜读丨那些被遗忘的时光
邓丽君:永不消逝的天籁之音
鲍勃·迪伦:永不落幕的明星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热映
《正版 鲍勃迪伦 永不落幕的明星 人传记真实经典音乐家人物传记书籍 名人现当代散文随笔书籍励志经典 江MU2ZM9》李·马歇尔著【摘要 书评 在线阅读】
温暖一生的声音,永不消逝!
不入全明星不是没实力!被遗忘的“北境之王”——德玛尔
张国荣,一位永远不会被遗忘的华语流行音乐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