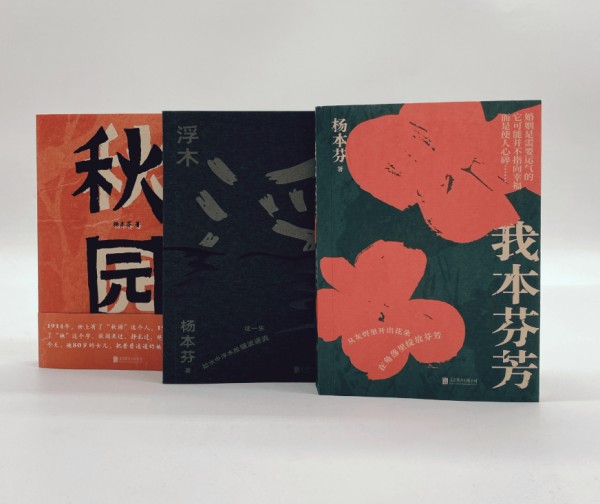对话音乐剧《面试》中文版主创:戏剧没有标准答案,它需要慢慢沉淀
过去几年来,版权合作项目在国内音乐剧市场的布局发生了转变。除了欧美经典IP,大量基于不同程度本土化改编的小剧场作品进入市场,影响着后续版权项目甚至原创剧目的发展方向。若将这种转变视为2020年后营商环境变化对演艺市场的倒逼,反观在此之前,包括《面试》在内的较早一批小剧场作品的引进,则体现出一定的行业前瞻性和市场预见性。从版权洽谈到舞台落地,看似常规的流程深刻塑造着行业的未来面貌。
日前,《面试》中文版结束了在北京的演出。我们与该剧导演施亦骏、音乐总监蒋哲光一从戏剧创作的角度出发,回顾创排幕后故事,探讨剧目的艺术生命力所在,以及版权项目对原创剧目的影响。两位受访者加入《面试》剧组的时间恰好对应了小剧场版权戏进入国内市场的不同阶段,并为我们提供了不同创作环节的视角。
以下为中国文化报记者与施亦骏、蒋哲光一的访谈实录,时间为2025年11月9日午,地点为北京世纪剧院。

音乐剧《面试》中文版剧照 上海音乐剧艺术中心供图
丁贵梓:《面试》从初排到新一轮复排已经有六年了,两位分别是什么时候加入的?
施亦骏:我是在第二轮加入的,2021年左右,那时我已经和中韩两边的制作方合作了另一部作品《烟雾》。当时国内观众已经知道《面试》这部戏了,我们聊了聊关于它的创作想法,目的性、指向性都比较明确,确定档期后就开始了合作。
蒋哲光一:我是这一轮新加入的。韩版初演时我就知道这部戏,它用音乐推动剧情,3个演员完成不同的音乐塑造。今年上海文广演艺集团联系到我,说想要复排《面试》,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那太好了,它在音乐剧市场中是比较有标志性的剧目,我们可以让前期积累的创作想法与新一轮的音乐碰撞出更不一样的火花。
丁贵梓:两位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加入《面试》,这期间的跨度刚好是大量韩国版权戏进入国内小剧场的五六年。
施亦骏:《面试》刚来的时候,市面上类似的作品还比较少。韩国小剧场作品的戏剧性比较强,就像早期很多观众会觉得《面试》是一部爽剧,一个人可以突然间塑造很多个角色。而且它的剧作严谨、舞美简单,让人耳目一新。到了2021年以后,上海引进了不少类似的戏。这一方面是因为韩国大学路的运行模式,比较适合我们去借鉴和发展;另一方面是比起百老汇经典剧目,这类戏的制作成本相对低一些,相应的硬件设施要求、排练时间要求也更灵活。
丁贵梓:然后就催生了演艺新空间模式,慢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悬疑题材项目。大哲站在自己的时间节点上,觉得《面试》跟现在市场上的作品相比有哪些优势呢?
蒋哲光一:2020年之前,《面试》在小剧场里是先锋的。它极具故事性,音乐与戏剧高度咬合,小体量、大能量。它证明了好故事是音乐剧的根本,它的音乐是戏剧动作的一部分。这给当时的观众和从业者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让大家看到了音乐剧作为一种综合艺术的内核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随着这几年小剧场的发展,我觉得《面试》在慢慢成为一种“经典的价值”。它的故事和音乐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扎实的剧作功底显得尤为珍贵。它成熟的创作方法论,告诉我们如何处理复杂心理叙事,如何构建音乐戏剧张力。音乐剧这种综合艺术,大家看的多了慢慢也会产生观念的转变。但无论市场如何变化,人类对于深刻情感和复杂人性的探究是不变的。《面试》能提供这种超越时间的情感共鸣,我觉得这是它持续吸引观众的根本原因。
施亦骏:我觉得艺术作品其实很难从市场角度去分析它的优缺点,因为它是一个作品,在讲述一个故事。作为创作者,我们如何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加精彩、好看,才是关键。我现在再讲述上世纪80、90年代的事情,如果能跟观众产生情感共鸣,那它就可以一直存在。这个作品放到现在,有观众喜欢、有观众不喜欢,我觉得都正常。但如果创作者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强行地做一些调整,去迎合或讨好观众,我觉得反而是一种泡沫,而且往往会失败。如果大家都在讨论今天的观众喜欢什么,就会发现市面上突然涌现出一批差不多的作品,都在分那杯羹。这样就好像在卖一个商品,违背了创作的本性。
我们要做的是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把作品做到高标准,去引领观众、引导观众欣赏艺术作品。我觉得做戏也好、演戏也好,它更多的是给到一个方向,而不是一个结果。这个方向可能有观众不喜欢,因为每个人经历不一样。但我们要尽量把故事讲好,讲得细致、严谨、有趣。要讲好故事,我们是讲故事的人。
丁贵梓:《面试》作为早期小剧场模式的初步探索,它的基本框架搭在这儿,我们可以用五六年的时间不断寻找新的点,但也没有必要刻意迎合一些短暂的市场风向。两位一位是导演,一位是音乐总监,其实是站在不同的环节上共同完成创作的。这次复排中,两位从创作层面上分别做出了哪些调整?
蒋哲光一:我觉得复排不是简单的重复,用剧中的台词来说,我们在音乐上“进化了”。这次调整的核心在于情感的精度与音乐的浓度。以上海站的演出为例,我们加入了弦乐组,希望在音乐的织体上做得更饱满、更有层次。弦乐带来的不仅是温暖,还有叙事感,它能勾勒出那些钢琴无法单独表现的、细微的情感纹理,让整个音响画面更具沉浸感和戏剧性。
丁贵梓:在这一版之前没有弦乐吗?
蒋哲光一:上一轮有过,我们也是在此基础上再抓细节,扣紧人物的不同性格。辛克莱变成吉米后,性格比较激进,弦乐乐手这时的功法和力度都是偏激烈的。当他变成胡迪,一个8岁的小男孩,弦乐就会变得很细腻、很温暖,让观众感受不同人物性格所匹配的音乐属性。
施亦骏:其实对我来说,没有所谓复排的概念。它像是一个台阶,如果在上一轮走到了第五层,我就希望下次能走到第六层或第七层。经过上一轮的演出后,还会发现演员之间化学反应新的处理。所以我这次给了很多角色细节上的新表达,而且比较开放式。我会告诉演员这个角色大的框架和背景,也会明确我要的是什么,在这个范畴里让演员去发挥。
每个演员的理解会很不一样,排练过程中,我们其实不断地在做一个游戏。如果你是这个角色,你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你8岁的时候遇到这种事,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排练的时候经常会说演员演得特别好,太棒了。或许我觉得有问题,但我会不断地引导演员,先让他发挥,当需要做一些减法的时候,再告诉他这个地方可能不合适。我排练的方式基本就是这样,排练厅非常热闹、非常好玩。我觉得音乐剧也好,其他戏剧门类也好,它本身是艺术。艺术创作应该是轻松愉快的,哪怕是再痛苦的故事,它的创作环境应该是轻松的。如果我们天天都很严肃,演员心里也会有压力,可能没有办法放松地展现自我。这就像个“骗局”,就像尤金对马特一样。
丁贵梓:放养似的。
施亦骏:对,艺术本身就是该放养的,圈养的话怎么产生灵感呢?它不是一个数学题,没有标准答案。
丁贵梓:或许在创作环节上不去考虑太多外在因素,才能帮助大家找到更多不同的解法,作品的艺术生命力会给出回应的。《面试》说到底是个版权剧,它的故事、音乐、人物,甚至立意都是既定的。在版权的基础上创作,要怎么处这其中的程度和界限呢?
蒋哲光一:针对这种版权戏,原作已经有很稳定的音乐框架了,我们需要在现有的音乐框架内注入属于我们的情感。原版音乐中,核心的戏剧结构和音乐动机是不可动摇的底线。这些是作品的骨架和灵魂,比如一个代表命运的主题旋律,它的出现、变形和发展是与剧情反转严密扣合的,改动它就会伤及根本。我们必须百分之百地尊重和还原。
在表演层面和情感表达上,我们会进行充分的本土化创作。韩国演员的表演方式、台词节奏未必完全适合中文语境和我们的演员,我们就会在这种地方进行一些微调。我会引导演员从中文的语感、中国观众的情感共鸣点出发,去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最真实自然的表达方式。这不是篡改,而是转化,是为了让这个故事的灵魂能通过我们的身体和声音,更顺畅地传递给当下的中国观众。
丁贵梓:所以版权方对于这种微调是可以接受的?
蒋哲光一:是的,而且我们的核心是保住底线,整个音乐的结构不变,在原有的音乐主题下。比如尤金催眠时标志性的音乐,我们都保留了。借助这些固定的动机,我们会发展一些更符合中文版的改编。
施亦骏:版权一般有一类版权和二类版权。一类版权就像百老汇的戏,我们可能连一个字都不能改,包括服装道具、灯光之类的。二类版权我们是可以改动的,这个幅度就会很大。但《面试》好像建立在一类和二类之间,很有意思。我们主创会先和制作部门沟通,了解能给到的创作范畴,也聊到作为创作者对新一轮改动的想法,希望能在创作层面上让我们往前走一走。比如要先确定演出规模,剧场调整后舞美变不变,有了这些改动我才能配合做出调整。这次是没有调整的,那我们就在这个范畴里去工作。
丁贵梓:是的,我原本以为《面试》进艺海大剧场以后,在舞美上会有调整。
施亦骏:我们与制作部门也有过沟通,制作和主创在综合考虑后,决定是在音乐上做调整,加入了弦乐。这一轮演出中途,韩版导演来上海看戏。其实这个戏在韩国现在也做了一些新的改动,他来上海以后发现看到的还是最早的舞美,很激动,说好像还是这个版本最能给他带来感触。
丁贵梓:我是在北京看的,虽然北京站没有弦乐,但整个看下来我觉得还是能撑满大剧场的。在开演之前我会觉得舞台很空,但开演以后就ok了。
施亦骏:大剧场和小剧场的区分,我倒不觉得是在景或人数上。这个剧本是可以承载各类规模的剧场演出的,只是可能给观众带来的观感体验会略有不同。作为创作者,也许我们想太多市场的东西也没有用,先把故事讲好了。
丁贵梓:最后一个话题是想跟两位聊一聊版权合作项目与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现在国内市场出现了很多版权合作项目,两位觉得当下我们的音乐剧行业可以从这些项目中学到什么?
施亦骏:学到他们先进的制作理念和流程,以及工作方式,如何用专业去与人沟通。不是因为你是导演、你是音乐总监,你在这个职位上就可以无端地给任何指令,这是不对的,而是要互相尊重每一个岗位。我们对音乐、剧本、角色的理解,一定要比演员清楚和详细得多,要非常明确自己在这个戏里想表达的世界观。
这个工作里有太多细节了,一周内如何安排排练计划?甚至于排练1个小时是不是需要休息10分钟?我们不断地在喂养信息,给到各个部门,他们再消化吸收,这是一个产业化的过程。我们通过跟一些引进剧组合作,慢慢知道了如何科学地安排排练计划。一周排多久,先排歌、先排戏还是先排舞蹈,学习他们相对完善的排练方式。当然,这些经验也是依据他们常年的工作总结而来的,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一些自己用得上的东西。
丁贵梓:我们现在行业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距离产业化还有一定距离。在这个阶段里,这些版权合作项目的一些先进经验是能给我们以借鉴的。
施亦骏:是的。有的时候大家其实不是很明确自己应该在每个时间段里做什么。艺术需要创作,但也不是无止境的,它也需要科学,各部门配合才能产生作品。
蒋哲光一:我还挺认同导演的说法。但是我觉得,现在基本上这个行业里都是“引进来”这种单一的模式,五年之后其实可能会有共生共育的成熟行业生态出现。“引进来”是重要的基石,有助于降低观众看戏的入门门槛,观众基本不会担心看版权戏踩雷,这也培养了观众的观剧习惯。作为创作者,我们也可以快速学习他们一流的制作流程、音乐的创作手法,甚至新技术的运用。
我觉得版权类的价值不止于只是我们做“复制”,而是可以催化原创剧目的生产。观众看了他们的剧,自然而然地会对标国内的原创音乐剧。我们应该利用这些合作,将其反哺到原创作品的开发中,提升行业标准,会有更多好的原创剧目出现。
施亦骏:在这点上我有些不一样的看法。我觉得五年之后也许会迎来一个大的泡沫期,引进剧不多,原创数量可能也会少。
蒋哲光一:怎么说呀?
施亦骏:音乐剧从世纪初的《妈妈咪呀!》《猫》开始,到现在差不多有十几二十年了,我们现在演的版权戏基本还是那时的那些剧。韩国小剧场也是一样,他们创作也是需要时间的。我们现在去韩国看戏,已经很少能看到自己觉得很好的小剧场作品了,可以引进的内容其实不多。
我们的音乐剧市场一下子发展太快了,但我觉得原创能力没有跟上。戏剧讲述生活、讲述人生,需要编剧、导演、演员花时间慢慢体验。它不是公式,也没有技巧。如果没有感悟到这种人生,是写不出那种歌的,只能抄那些旋律而已。我们还没有找到能培养出强大原创能力的土壤,我们没有在讨论对生活的理解、对音乐的理解、对人生的理解,讨论的是观众喜欢看什么。再加上现在一下子涌出来很多作品,可观众数量并没有增加很多,这条路就会越走越窄。年龄层也越来越年轻,当然这也可能是好事情,能有更多年轻人进入这个行业。这就要看我们下一步怎么走了,不然就会等来一个强大的泡沫期。
丁贵梓:其实我和导演的观点差不多,我们这两年的步伐有点太快、太急了,市场推着所有人往前走。
施亦骏:太好了,那你准备什么时候改行?(笑)这个行业是会有分流期的。我最早是做话剧的,上海话剧市场也经历过这种变动,国外IP和悬疑题材吸引了一波小范围的观众,然后出现了一批民营制作团队,后来慢慢都消失了。过了10年,我又在上海音乐剧里看到了这种情况。
丁贵梓:多年前,上海话剧市场也有类似的发展经历吗?
施亦骏:上海的商业话剧,留下的很多还是早期项目。市场在变,市场里的产品没有变。现在我们承载不了这么多的制作公司和作品,也没那么多观众。通过学习版权戏,我们是可以做出很棒的创作作品。但如果只是偶尔有几个,那就还没有形成常态。
丁贵梓:只能相信大浪淘沙的能力,大家尽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一起慢慢让这个行业变得更好。
施亦骏:正所谓“乱世出英雄”,大哲靠你了。
蒋哲光一:我努力,一起努力。
责编:孑一
网址:对话音乐剧《面试》中文版主创:戏剧没有标准答案,它需要慢慢沉淀 https://m.mxgxt.com/news/view/1885115
相关内容
音乐剧在中国:梦想指路,慢步向前对话李安:各种解读没标准答案 信仰很重要(2)
对话缪时客|版权+原创,如何让音乐剧“两条腿走路”?
音乐剧在中国:梦想指路,慢步向前 ©️深响原创 · 作者|王萌“实在不行找个班上吧。”2020年初,大半年没有演出和排练,完全断掉收入的音乐剧演员周仕麒就...
对话上海文化广场|音乐剧的剧场怎么做?
为什么要看原创音乐剧《赵氏孤儿》?剧院给你答案
对话缪时客|版权+原创,如何让音乐剧“两条腿走路”? ©️深响原创 · 作者|王萌2024开年,音乐剧制作公司缪时客发布了一组年度剧单,将过往作品按照类型、原著、体量等标准细...
《热浪之外》对话刘震云:凡是好东西都需要慢慢生长
2019音乐剧明星集锦音乐会主演见面会音乐剧演员没有大咖一说
2019音乐剧明星集锦音乐会主演见面会 音乐剧演员没有大咖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