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托·巴斯托斯:用文学收集大灾异之后,无名者们的哭声
巴斯托斯以其书写巴拉圭历史的长篇小说三部曲《人子》(1960)《至上者》(1974)和《检察官》(1993)闻名。作为拉美文学爆炸运动的后起之秀,巴斯托斯的代表作《至上者》,被英国拉丁美洲小说研究专家杰拉尔德·马丁认为是一部可与《百年孤独》媲美,甚至比其更具历史重要性的巨著。

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1917-2005),巴拉圭著名小说家,20世纪最重要的拉丁美洲作家之一,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时期代表人物,著有多部小说、电影剧本与诗集,代表作有《人子》《至上者》《检察官》等,1989年获西语文学大奖“塞万提斯奖”。
在《至上者》中,后现代书写的混杂、多元与开放达到极致。一面是掺杂着本地瓜拉尼语语法及词汇的对白在纸页上涌现,一面是档案、诗歌、脚注的引入,在提示着读者这一叙事文本的不可靠性。书写的痕迹被刻意保留,词语仿佛被刚刚浇铸出来一样,带着温热的浇口。透过对巴拉圭历史上的“至上者”何塞·弗朗西亚内在世界的描绘,巴斯托斯编织出了一件光怪陆离的词语织绵。纷繁复杂的叙事技巧,与作者对现实与历史的强烈介怀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这样一部兼有元小说与历史小说特点的奇书。
撰文 |谈炯程
战争与独裁的轮舞
状如象耳的南美大陆上,巴拉圭似一块细小的胎记横卧于中央。这一位于内陆的葺尔小国,在17世纪时,曾是耶稣会在南美洲活动的中心。巴拉圭河、巴拉那河及其支流,仿佛血管般为其输送养分。透过河流,如今的巴拉圭可以通达世界,进入全球化市场体系之中。但过去几个世纪,这里都是一片封闭的边缘地带。19世纪初,巴拉圭从宗主国西班牙手中取得独立。嗣后,从弗朗西亚,到继任的洛佩斯父子,再到其后的一系列军人总统,巴拉圭被套上一副又一副独裁的重轭,经济停滞,闭关锁国。19世纪70年代,在小洛佩斯的一意孤行下,该国滑向一场悲剧性的三国同盟战争。战争从1864年持续至1870年。地寡民贫的巴拉圭,以一国之力,对抗阿根廷、巴西帝国及乌拉圭组成的联军。虽然战争最初阶段,巴拉圭军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因为国力差距悬殊,巴拉圭在付出巨大伤亡代价之后,依然战败,整片国土几乎都化为焦土。纵观整个拉丁美洲史,三国同盟战争都是最血腥的一场战争。战后,巴拉圭的人口锐减至战前的一半,并丧失25%至33%领土。
巴斯托斯正是诞生在这样一个在战争与独裁的轮舞中挣扎的国家。之于他,小说是承载集体记忆的器皿。透过书写,作家直接回应历史与当下。他曾自述道:“文学活动逐渐意味着直面命运的必要性,意味着投身于集体的生机勃勃的现实、其真实的道德背景和社会结构以及当代现实的复杂关系之中的意愿——也就是说,文学意味着,将自身投射到普遍的人类世界中。”是以巴斯托斯最广为人知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即从不同角度,拓写了巴拉圭的过去与现在。《人子》以宗教故事为壳,讲述1912年至1936年巴拉圭的民生百态;《至上者》深入巴拉圭第一位独裁者弗朗西亚的内心,探究巴拉圭历史灾难的原点;《检察官》则从一个反抗者的角度,描写了1954年至1989年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统治之期间的诸种暴行。
他并非仅在书斋中,透过对案头文件、历史档案的裁剪进行书写。一次又一次,巴斯托斯被迫进入拉丁美洲近现代史的暴风眼,不得不和一众拉美作家一样,踏上流亡之旅,先是于1947年红白两党内战期间因公开反对总统伊吉尼奥·莫里尼戈,而被迫与50万巴拉圭同胞一道,逃往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后又因阿根廷独裁者豪尔赫·魏地拉的上台,于1976年出走法国,定居于图卢兹,在图卢兹大学教授瓜拉尼语和西班牙文学。1982年,巴斯托斯遭遇了巴拉圭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政权的“绝罚”,他们以莫须有的颠覆罪名,禁止其回到巴拉圭。直到7年后,该政权垮台,他才在新领导人安德烈斯·罗德里格斯的邀请下,重返故土。

巴斯托斯。
包括长篇小说三部曲在内,巴斯托斯的绝大多数代表作都写于流亡途中。他曾表示:“流亡除了让我产生对暴力和贬低人类境况的厌恶之外,还让我感受到了人类境况的普遍性。流亡让我从他人的视角了解自己的国家,并以此为视角去体会它所遭受的巨大不幸。”
在此之前,出生于1917年的巴斯托斯,作为一名医疗辅助人员,亲历了1932年至1935年的查科战争。彼时,巴拉圭与玻利维亚两个内陆国家,为争夺大查科地区的石油资源爆发冲突。战争最终导致两国十余万人死亡,是20世纪拉丁美洲历史上最致命的战争。青年巴斯托斯原本梦想着“在战火中获得净化”,而他迎面所撞见的现实却是两个兄弟国家的平民,在半干旱的荒漠里自相残杀。这段火线上的经历,是小说《人子》的重要素材来源。这部长篇小说,为巴斯托斯赢得了评论界及普罗大众的广泛青睐。它对巴拉圭重大历史时刻的关注,其多线叙述的技法,瓜拉尼语与西班牙语彼此交织互渗的巴洛克式繁复文风,都被《至上者》继承了下来。
《人子》以细密画般的笔触,透过各种碎片化的小叙事,摹写出战争与独裁在巴拉圭人身上留下的刻痕。但与《至上者》相比,创作《人子》时期的巴斯托斯,尚未充分开掘权力和书写这一母题。此种母题,将是1960年代至1970年代在拉丁美洲勃兴的“独裁者小说”的核心关注点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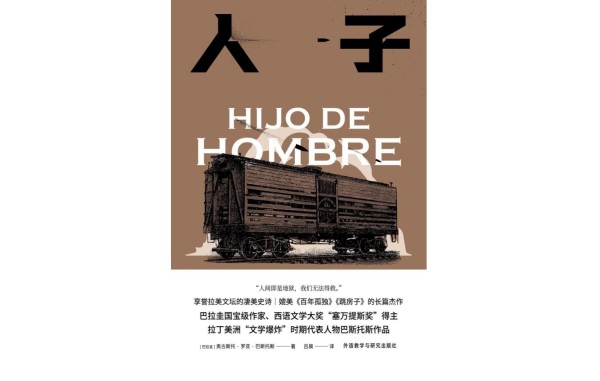
《人子》
作者:[巴拉圭]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
译者:吕晨
版本:互文·雅众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1年11月
拉丁美洲作家书写独裁统治的传统,最早可追溯到阿根廷第七任总统、作家兼记者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于1845年创作的非虚构作品《法昆多:文明与野蛮》。该书描绘了1820年代至1830年代统治阿根廷各省的军事领袖胡安·法昆多·基罗加的生平。在《法昆多》中,文明与野蛮构成一组对位法。代表文明的,是北美,是城市,是一神论信仰以及欧洲;而与野蛮连接在一起的,则是乡村、亚细亚与西班牙的专制主义、联邦党人、拉美传统和奉行强权的法昆多们。如此粗糙的二分法,显然并不能反映文明与野蛮之间纠缠互渗的复杂关系。但正是《法昆多》提出的此种二元辩证,成为了塑造后殖民时代拉丁美洲文化的重要内驱力。包括巴斯托斯在内,许多拉美作家都在自己的写作中回应着《法昆多》的命题。他们不再认为拉美本土以及广阔而贫穷的乡村腹地是幽暗且野蛮的。譬如,《人子》即把《法昆多》沾染着进步主义迷思的预设翻转,将未受教育的主角克里斯托瓦尔·哈拉视作“人子”的化身,而将出身优渥的革命支持者米格尔·维拉,塑造成一位彷徨延宕的“哈姆雷特”。
危地马拉外交官兼作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也透过对危地马拉传说的梳理与整合,从本土文化的根系处理解其祖国。他写于1933年、出版于1946年的长篇小说《总统先生》,被评论广泛视为“首部真正意义上的独裁者小说”。这部小说,以后来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而非当时占主流的历史现实主义手法写成。它创作于阿斯图里亚斯留学法国期间,因此亦受到彼时方兴未艾的法国超现实主义的影响。“独裁者小说”的基本范式,在阿斯图里亚斯手中已然初现雏形。这些小说大多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弱化叙述的因果关系模糊现实与想象的边界,并以独裁者或独裁统治下的社会心态为摹写对象。
拉美文学爆炸后期,许多拉美作家都选择重写以《总统先生》为代表的“独裁者小说”。他们在阿斯图里亚斯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开始关注书写与权力的关系。《总统先生》里那位空气般无处不在却时刻隐形的总统,在诸如《至上者》《族长的秋天》一类的“独裁者小说”中显影。作家们分毫毕现地描绘这些独裁者内在世界的空洞、孤独与恐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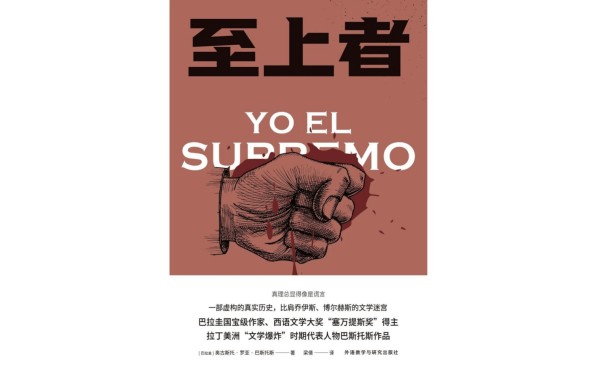
《至上者》
作者:[巴拉圭]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
译者:梁倩
版本:雅众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4年7月
加西亚·马尔克斯1975年出版的《族长的秋天》和巴斯托斯的《至上者》,都有着河流般绵长的句子,逗号在这些永无尽头的长句中,仿若一尾尾溯流而上的鳟鱼般跃起。绵密的叙述之流几乎要让读者透不过气来。《族长的秋天》绝大部分篇章,用有限制的第三人称视角写成,尽管那些由长句黏成的几乎不分段的长段落十足挑战读者的耐心,但叙述视角中和了叙事的密度。碎片化的叙事之外,人们依然可以找到作者留下的语言的脚手架,继而将叙事拼图一片片组合起来,以抵达那个最核心的关于权力与迷失的故事。
《至上者》则不然。该书中许多篇什,由弗朗西亚与其秘书帕蒂尼奥之间的对话构成。这些对话没有以引号括出,而是如密码本中的密码般堆叠在一起。个中原因在于,虽然引号可以清晰地标出对话中句子的归属,但它们也将独裁者与秘书间近乎神经质般亢奋的词语之流,将那混合着西班牙语与瓜拉尼语两种语言的特质的高密度对话,肢解为一个个乏味的,孤立的语言碎片。
透过这绵绵不绝的对话,透过这对话中《项狄传》式的离题,透过时空的混杂交错——弗朗西亚甚至谈论起自己未来的死亡,以及发生在他身故80余年后的查科战争——巴斯托斯以其精心创造的不可靠叙事,抵达了一种元小说的书写。《至上者》开始于弗朗西亚博士对一则假托其姓名的伪造文书的追寻。这位意欲掌控文字,并利用文字主宰历史与记忆的独裁者,忽然意识到自己竟也会被文字隐而未显的力量颠覆。因此,某种程度上,马尔克斯与巴斯托斯笔下独裁者的处境,构成了对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全知叙述者的隐喻。他们的书写透露出对秩序的渴望,一切词语,一切语言以及一切人物,它们的出现,仿佛都要作用于塑造一种堪与现实比肩的虚构。“19世纪的小说家不厌其烦地发明和结合各种方法,使读者产生更直接和更彻底的幻觉。”法国学者亨利·戈达尔在《小说使用说明》一书中写道:“为此,他们建造了一座叙事手法宝库,包括叙述视角、自由间接体等等。这些手法的运用使读者能与小说人物有更亲密的接触,遗忘叙述者的存在。”而现代小说的革新之处,就是要拆除此种虚构的地基,质疑现实主义的基本预设,从而抵达对书写本身的思考。

《至上者》中所写的19世纪巴拉圭独裁者弗朗西亚。
作为一种抵抗的书写
在小说里,书写既能够塑造权力,也能够颠覆权力。词语背后,争夺集体记忆的战争从未停止。《至上者》中,当弗朗西亚让秘书在词典中查找“quimera”一词时,秘书回答道:“大人,字典里写着幻觉,胡思乱想,幻想。”之后,两人开启了一段如禅宗语录般的对话:
“在现实中,在纸上,我正在逐渐变成这样。大人,这里还写着:传说中有着狮头、羊身、龙尾的怪物。他们说,我过去是如此。大人,词典里还有补充:一种鱼或蝴蝶的名字;争执,口角。所有这一切都曾是我,又都不曾是我。词典是埋葬空话的坟地。”
借弗朗西亚之口,巴斯托斯思考着小说语言的本质,以及权力对语言的扭曲,他写道:“我们人类用虚幻空洞的原料发明的语言,我们为此自豪,可这些原料却毫无根据,与生活毫不相干。”而他所寻找的语言,是能够自行发声的语言,在此种语言中,“词汇像事件一样发生”。这是一种意义寡淡,能指与所指如皮包骨般结合在一起的“新话”,一种只有名词和铰链般铮铮作响的动词,而没有形容词润滑的,缺乏颜色的语言。
由是,这位“至上者”在巴斯托斯笔下,变成如同柏拉图的哲人王一般矛盾的存在。历史上的弗朗西亚也确实如此,他意图以其拥有的绝对权力,依照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构想,将巴拉圭打造为一个属于穷人的乌托邦。这大抵是因为,1780年代在科尔多瓦国立大学攻读神学与哲学博士学位期间,弗朗西亚受到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思想的濡染。伏尔泰、卢梭的著作以及《百科全书》,他都如数家珍。后来,弗朗西亚放弃了神学,转而修习法学,并开始其作为律师的执业生涯。期间,他一直为殖民地下层阶级的权益奔走呼告。他的民粹主义观点,也在这一过程中被强化。
拉丁美洲学者安东尼奥·德·拉·科瓦如此评价弗朗西亚的统治,在他的政权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奇特的混合体:能力与任性,远见卓识与鲁莽迷恋,追求崇高理想的不懈努力与公然违反最简单的正义原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似乎变得更加专制”。这或许正是伏尔泰念兹在兹的“开明专制主义”,即透过一位笃信启蒙主义的君主,自上而下地改造原有的社会结构。但在后殖民条件下,此种“开明专制主义”的遗产必然是苦涩的。三国同盟战争的惨痛教训与嗣后的巴拉圭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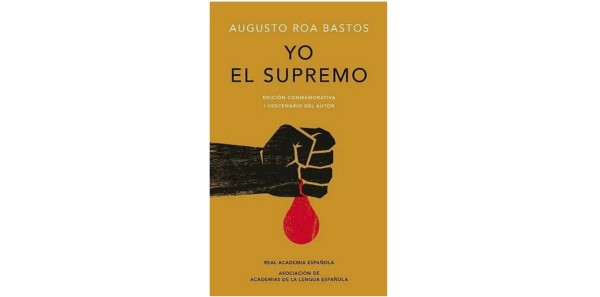
《至上者》外文版封面。
这样一位信仰民粹主义与启蒙主义的独裁者,其对知识的态度必然是矛盾的。在弗朗西亚治下的巴拉圭,书籍是与军火并列的少数免税商品。1828年时,他曾规定,所有巴拉圭男性必须接受国家教育。在此之后,巴拉圭的文盲率逐步下降。但另一方面,此种推广国家教育的举措,亦可视作权力向社会毛细血管的渗透。在《至上者》中,巴斯托斯尖锐地指出,独裁者们往往倾向于相信,他可以随心所欲地重塑历史,划定其边界,规定其意义。对书写,尤其对历史的书写的垄断,是他们权力合法的来源。
而之于巴斯托斯,小说则构成了一种作为抵抗的书写。他身为作家的道德义务,是收集历史的大灾异之后,那数不尽的无名者的不曾被倾听的歌哭,以使其词语,化作漫漫长夜中的微弱见证。诚如俄裔美国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在《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或曰浮起的橡实》一文所说的:“文学是社会所具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险形式;它是一种针对弱肉强食原则的解毒剂;它提供一种最好的论据,可以用来质疑恐吓民众的各种说辞。”
《至上者》正是这样一本有着解毒剂效应的小说,透过对弗朗西亚充满矛盾的内在世界的描绘,它勾勒出贯穿巴拉圭,乃至整个拉丁美洲近代史的基本矛盾。在这片土地上,启蒙主义与后殖民现实、文明与野蛮、本土传统与欧陆文化之间,总是互相纠缠,如同难以解开的“戈尔狄俄斯之结”。文学或许无力像刀刃一般劈开它,却可以在词语层面,为弱者赋权。
作者/谈炯程
编辑/张进
校对/赵琳
网址:奥古斯托·巴斯托斯:用文学收集大灾异之后,无名者们的哭声 https://m.mxgxt.com/news/view/1850838
相关内容
奥托·梅斯莫奎托斯
奥斯卡·多斯桑托斯·恩博亚巴·朱尼奥
阿撒托斯
世界百名文学大师排行榜,中国三人鲁迅排93,俄罗斯四人托尔斯泰排名第4
赫菲斯托斯
巴西演员费尔南达·托雷斯受邀成奥斯卡奖评委成员
费兰托雷斯和贡萨洛拉莫斯,20年后有可能超越老托雷斯和拉莫斯吗
托马斯·桑斯特
桑托斯明珠·球迷的宠儿·传承桑巴足球的“舞”者——内马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