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楼梦考证》看胡适对中国学术研究范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
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看似只是针对一部古典小说的考证文章,却暗藏着一场学术革命。当时的中国学界,"索隐派"红学盛行,王梦阮、蔡元培等人热衷于将《红楼梦》人物附会到历史人物上。胡适却别开生面,以科学方法考证《红楼梦》的作者、版本等基本问题,不仅为小说研究提供了新路径,更是在中国传统学术土壤上播下了现代学术研究的种子。他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为治学方法,挑战了传统学术的权威,为中国学术研究范式的现代化进行了一次勇敢的探索,也为《红楼梦》的经典化奠定了基础。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绝非偶然之作,而是其个人学术兴趣、思想方法以及时代背景共同作用的结果。要理解这部开创性著作的出现,就必须从多个层面剖析其写作缘起。
首先,胡适自小就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怀疑精神"。在《四十自述》中,胡适回忆自己十几岁时就有强烈的怀疑倾向,尤其反对家乡烧香拜佛的迷信行为。这种怀疑态度成为他日后治学的基本精神。在晚年口述自传中,胡适将这种"怀疑倾向"视为其治学方法的最初萌芽:"我对我的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理论、记载和事实,如一有怀疑,也都要予以批判来证明或反证明。这都是由于我的怀疑的倾向所致。"
这种怀疑精神在1910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当年,胡适在北京参加庚款留美考试时,在二哥同学杨景苏家第一次接触到汉朝的古典治学方法——汉学。他在阅读《十三经注疏》时,对汉儒解释《诗经》中"予"字的做法产生怀疑,认为汉儒所依据的《尔雅》并非古字典,而是出于汉儒自己之手。于是,胡适写了第一篇解决这个怀疑的文章——《诗三百篇言字解》(1911),尝试用归纳法来考证。此后,他又写了《尔汝篇》(1916)和《吾我篇》(1916)两篇研究代名词的文章,开始形成自己特有的治学方法。
胡适的学术方法还受到了美国留学期间几位重要学者的影响。康奈尔大学布尔教授的"历史的辅助科学"和乌德瑞教授的"高级批判学",以及赫胥黎的"存疑主义"和杜威的"实验主义"思维术,都成为他治学方法的重要养分。结合这些思想,胡适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治学口号——"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917年归国后,他将这套方法运用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研究中,1920年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考证文章《〈水浒传〉考证》,直言自己因"历史癖"和"考据癖"而爱做"半新不旧的考证"。
其次,胡适考证《红楼梦》的重要动机是要挑战当时盛行的"索隐派"红学。在胡适开始研究《红楼梦》之前,社会上流行的是以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1916)、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1917)和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1919)为代表的"附会的'索隐学'"。这些研究试图将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附会到历史人物身上,在胡适看来是"非科学"的。他认为,这些人"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胡适与蔡元培的争论焦点并不在结论上,而在研究方法上。他想通过提供科学的研究方法来取代这种穿凿附会的索隐方式。正如胡适所说:"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在消极方面,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柳泉一班人的谬说。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断,有充分证据而后信。"
第三,《红楼梦考证》与当时的"整理国故"运动密切相关。1919年12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开启了整理国故的思潮。1923年1月《国学季刊》创刊时,胡适进一步提出整理国故的三个方向:用历史的眼光扩大国学研究范围,用系统的整理部勒研究资料,用比较的研究帮助资料整理与解释。这场整理国故运动本质上是文学革命的继续,而"考证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则是整理国故的重要部分。胡适将此视为"具体而微的哥白尼革命",意在将汉学研究的范围扩大,打破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
最后,胡适考证《红楼梦》还有一个实际目的:提高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胡适认为,仅仅赞美这些小说的价值是不够的,还应该"采取更有实效的方式"。他建议:"我们推崇这些名著的方式,就是对它们做一种合乎科学方法的批判与研究,也就是寓推崇于研究之中。我们要对这些名著作严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历史探索——也就是搜寻它们不同的版本,以便于校订出最好的本子来。"这种做法可以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使它们成为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

亚东图书馆为《红楼梦考证》的问世提供了传播条件。1921年5月5日出版的亚东"初排版"《红楼梦》以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初稿)》作为导言,明确打出"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的口号,成为胡适传播科学思想方法、整理国故的重要平台。
归根结底,正如胡适自己所说:"我以'序言'、'导论'等不同的方式,为十二部传统小说大致写了三十万字考证文章。那时我就充分的利用这些最流行、最易解的材料,来传播我的从证据出发的治学方法。"《红楼梦考证》正是这一学术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胡适推广科学治学方法的媒介,也是他提高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地位的工具,更是他探索中国学术研究现代范式的试验场。
国故重估与方法革新
《红楼梦考证》不仅在研究对象上具有创新性,更重要的是体现了胡适对现代学术研究范式的探索。这种探索基于对"国故"研究观念、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全面重新厘定,成为整理国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理解《红楼梦考证》的学术视野,必须深入考察胡适的整理国故理念。
在胡适提出整理国故之前,社会上普遍认可的"国故""国学"仍然是承继清代以来"以儒为尊"的经学、史学研究。正如当时的史学家蒙文通所描述:"近二十年间汉学的派别很多,可说是清朝一代的缩影…什么教科书、新闻纸,一说到国学,便出不得这两派的范围。"在这种背景下,胡适如果想对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体制进行变革,就必须首先重新厘定"国故""国学"的研究对象,打破附加于这两个词上的各种"偏见"。
首先,胡适用"国故学"替代"国学",剥离了"国学"在晚清以来被赋予的民族主义色彩。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胡适指出"国故"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这样一来,"国故"就不再具有优劣之分,"一切中国过去的文化历史"都可称为"国故",研究这些文化历史的所有学问都可称作"国学"。
其次,胡适提出用"历史的眼光"打破"以古为尊"的评判标准。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箴言成为历来治学者崇古贱今的理论基础。胡适在《发刊宣言》中表明所谓"一切中国过去的文化历史"应"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何谓"历史的眼光"?就是他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所说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每一个时代,还他那个时代的特长的文学,然后评判他们的文学的价值"。这种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历史的眼光",以科学之名义否定了"以古为尊"的传统评判标准,大大扩展了"国故学"研究对象的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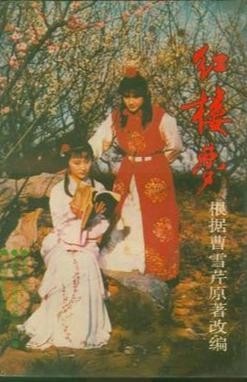
第三,胡适提出以"为真理而真理的态度"否定古人"通经而致治平"的治学目的。"经学"之所以一直占据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中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被赋予了经世治国的特殊使命。当胡适尝试建立全新的现代学术研究体制、打破经学的垄断时,传统学术的功利性便成为突破口:"我以为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做学问的人当看自己性之所近,拣选所要做的学问,拣定之后,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在此,他重新定义学术的目的:不在于是否能经世治国,而在于求索真理。这样一来,学术研究对象是不是"五经"就并不重要了,关键在于研究对象是否接近真理。
在扫除了附加于传统学术上的种种"偏见"后,胡适开始重新厘定"国故学"的研究对象。相较于传统学术研究对象范围,胡适的一个重要拓展便是将向来不被重视的民间文学,尤其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纳入"国故学"研究的范围。他认为"庙堂的文学固可以研究,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吴敬梓、曹霑和关汉卿、马东篱和杜甫、韩愈有同等的位置"。
胡适为清华学校胡敦元等准备留学国外的学生开列的国学书目就包括属于文学史之部的明清两朝小说。此后在《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中,他仍然保留了《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这四部白话小说。这一做法引起了梁启超的不满,梁启超认为这"挂漏太多,博而寡要",特别指出:"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而梁启超自己列出的"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中仍然是"四书"、《易经》《诗经》《史记》《杜工部集》等经史子集类,并未列入小说。甚至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梁启超明确指出:"吾以为苟非欲作文学专家,则无专读小说之必要。"由此可见当时有关"国学"研究对象的争议之一斑。
除了在研究对象上重新厘定"国故学"的范围,胡适探索现代学术研究范式的另一着眼点在于研究方法的革新。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中阐述了"整理"的具体含义:"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这种研究方法在"系统性"和"科学性"两方面区别于中国古代的传统治学方法。
所谓"系统性",按胡适所言,便是"历史的方法",他称之为"祖孙的方法"。这一方法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孤立的东西,而是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它产生的原因,一头是它产生的效果,要追溯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将材料组织与贯通。胡适认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最大弊病之一便是太注重局部的功力而忽略了整体的贯通:"清儒有鉴于宋明学者专靠理解的危险,所以努力做朴实的功力而力避主观的见解。三百年之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
而"科学性"则体现在"实验的方法"上,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将杜威的"实验主义"与乾嘉朴学"实验的方法"予以中西化合,并给这种中西化合的研究方法冠以"科学"之名:"科学的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由于"科学"一词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具有无上尊严的地位,这一命名使得这种研究方法容易被当时新、旧两派学者接受。
通过从研究观念、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层面重估传统学术研究,胡适提出了一套具有现代色彩的学术研究范式,并将之用于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考证研究,《红楼梦考证》便是这一现代学术研究范式的重要实践成果。
科学考证的示范
以上述胡适所创的现代学术研究范式为基础,《红楼梦考证》成为这一范式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通过对《红楼梦》的考证研究,胡适不仅为这部小说在现代学术研究体制中找到了合法地位,更通过自己的研究方法创新,为后来的学者树立了一个学术研究的范例。

胡适首先在研究观念和研究内容上,将《红楼梦》视为"创造的小说"并纳入现代学术研究的范围。他把《红楼梦》研究纳入国学研究,赋予其现代学术之荣誉,这为此后众多名人学士以严谨的学术态度研究《红楼梦》提供了合法的前提。正如胡适所言:"譬如讲《红楼梦》,至少我对于研究《红楼梦》问题,我对它的态度的谨严,自己批评的严格,方法的自觉,同我考据研究《水经注》是一样的。"这种态度上的转变意味着《红楼梦》研究发展成为"显学"之一的红学,被注入了现代学术内涵。
那么,如何研究《红楼梦》这样一部小说呢?胡适的方法论革命首先表现在对《红楼梦》性质的定位上。"索隐派"之所以采用附会的方法研究《红楼梦》,根本上是因为他们仍然以稗官野史之传统小说观来看待这部作品,认定其中必有影射历史的微言大义,强调作品与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而胡适则认为,《红楼梦》属于"创造的小说",这一定位充分肯定了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
基于这一定位,胡适提出了研究《红楼梦》的方法:"对这种第二类的小说,我们必须用一般历史研究的法则,在传记的资料里找出该书真正作者的身世;他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状况。"在《红楼梦考证(初稿)》的开篇,胡适就指出,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
基于这一认识,胡适将《红楼梦》考证的范围确定为"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一研究范围的确定,从根本上扭转了《红楼梦》研究的方向,使之从附会猜测转向了科学考证。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胡适运用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实验主义方法。以他考证《红楼梦》作者为例,胡适先根据书中第一回关于作者、书名的叙述,作出大胆假设:"大概'石头'与空空道人等名目都是曹雪芹假托的缘起,故当时的人多认这书是曹雪芹做的。"随后,他以袁枚《随园诗话》卷二中的记录为可靠旁证,得出"乾隆时的文人承认《红楼梦》是曹雪芹做的","曹雪芹是曹楝亭的儿子"这一初步结论。
接下来,胡适运用演绎法,由此"假设"展开对作者曹雪芹的考证。由于缺乏曹雪芹的直接材料,他采用了历史的方法,上溯查考袁枚所记载的"曹雪芹父曹寅"的材料,通过归纳法总结,考知关于曹雪芹家世、家庭环境、生活时代的情况。再以小说文本中的相关叙述来互证,通过对所有考证材料的组织贯通、综合理解,得出"《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的结论。胡适又根据作品中提及的康熙帝南巡事、袁枚言随园乃大观园等材料,再次确证他所得出的"自叙传"结论,最后归纳总结关于"著者"考证的结论。
这一考证过程清晰地体现了胡适所倡导的科学研究方法:首先使用归纳法,从个例观察中提出大胆假设;然后运用演绎法,以假设为基础展开求证;最后得出经证据证实、合乎逻辑的可靠结论。贯穿其中的是怀疑、批判的现代学术研究精神。正如胡适自己所说,科学方法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
此后,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胡适不断修正自己的考证结论,这种开放性的研究态度也是现代学术研究的重要特征。例如,在《红楼梦考证》(初稿)中,胡适认为曹雪芹是满州正黄旗人,而在后来的研究中,他修正为"汉军正白旗人"。这种基于新证据不断修正结论的态度,体现了科学研究的开放性和自我纠错机制。
同时,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还提出了此后红学研究的诸多基本命题,为一个专门之学的体系建立奠定了基础。他明确了考证研究的正当范围:"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基本命题为后来红学中的曹学、版本学、探佚学等分支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
胡适以科学的考证法为现代红学体系之建立提供了一套具备可操作性的系统研究方法,这为《红楼梦》步入现代学术的大雅之堂奠定了基础。与当时其他对《红楼梦》的研究相比,胡适的考证研究不仅内容丰富、材料详实,而且方法科学、逻辑严密,这种学术研究的示范作用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根本上看,胡适通过《红楼梦考证》实践了他的学术理想:以传统学术中考据学的形式,结合西方现代科学精神,创造一种新的学术研究范式。他不仅用这种范式为《红楼梦》在学术研究领域赢得了应有的地位,还通过这一具体案例向世人展示了现代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红楼梦考证》超越了一般的文学研究著作,成为中国学术研究范式现代化探索的重要标志。
红学蝶变新生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在发表后引起了广泛反响,这篇看似只是考证一部小说的文章,实际上却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小型革命。它不仅为《红楼梦》走向经典化铺平了道路,也为中国学术研究范式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实例。这一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尤其是在学术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变革效应。
首先,《红楼梦考证》为《红楼梦》步入现代学术研究体制开辟了道路。在胡适之前,《红楼梦》虽然备受读者喜爱,但在学术界的地位却相当尴尬。传统士大夫阶层一向不把小说视为正统文学,一些文人或许私下赏读,但很少会将其与经史子集等"正统"典籍相提并论。而胡适则通过《红楼梦考证》,将这部小说纳入了国学研究的范畴,赋予其学术研究的合法性。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正如余英时所言:"如果说清末的'红学'还只是一种开玩笑式的诨号,1921年以后'红学'(亦称'新红学')则确实已成为一种严肃的专门之学。由于胡适的提倡,《红楼梦》的考证工作已和近代中国学术的主流——从乾、嘉考据学到'五四'以后的国故整理——汇合了。因此,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红学'无疑地可以和其他当代的显学如'甲骨学''敦煌学'等并驾齐驱,而毫无愧色。"这一评价准确地指出了《红楼梦考证》对红学学科建立的关键作用。
统计数据显示,自胡适《红楼梦考证》出版后,越来越多的学界人士开始以严谨的学术态度研究《红楼梦》。仅在1920年至1930年这十年间,关于《红楼梦》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就达到了一百多种,这一数字在当时的学术界是相当可观的。俞平伯、李辰冬、李长之、周汝昌、李玄伯等后来成为红学界知名的学者都是在这一时期加入红学研究的行列,而且他们的研究多多少少都受到了胡适的影响。
以俞平伯为例,他原本并没有研究《红楼梦》的兴趣,但通过顾颉刚了解到胡适考证《红楼梦》的一些情况后,竟慢慢提起兴味来,开始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研究方法来做《红楼梦》的版本勘定工作。俞平伯后来成为红学界的重要学者,他的《红楼梦辨》等著作对红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不仅如此,《红楼梦》的讲授也开始进入大学课堂,成为正式的学术研究对象。1920年,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马裕藻聘请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所用讲义《中国小说史略》中有关《红楼梦》的章节也大量征引了胡适《红楼梦考证》的结论。这表明胡适的研究成果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成为相关领域的权威参考资料。
其次,胡适《红楼梦考证》所提出的一套系统问题和研究方法为"新红学"的创立打下了坚实基础。尽管这套方法的"科学性"在后来的学术发展中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但不可否认的是,以科学考证法来研究《红楼梦》确实是"新红学"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红学之所以能成为显学,其学术性的体现与胡适所开创的以现代科学考证法研究《红楼梦》密切相关。
在胡适之前,红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小说内容的解读和评论上,特别是"索隐派"红学热衷于将小说人物和情节与历史事件和人物对应起来。而胡适则将研究重点转向了文本本身的历史考证,包括作者考证、版本考证、写作过程考证等。这种转向不仅拓展了红学研究的范围,也使得红学研究向着更为科学、系统的方向发展。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提出的研究范围,即"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成为后来红学研究的基本命题。基于这些命题,后来的红学研究发展出了曹学、版本学、探佚学等多个分支,逐渐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学科体系。
此外,胡适的考证方法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他那"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论,以及对材料的系统整理和分析的做法,成为许多研究者效仿的对象。即便是对胡适的研究结论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在研究方法上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他的影响。
第三,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胡适通过《红楼梦考证》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学术研究范式的现代转型尝试。他将西方科学方法与中国传统考据学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新的学术研究范式,这种范式既保留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特质,又吸收了西方现代学术的精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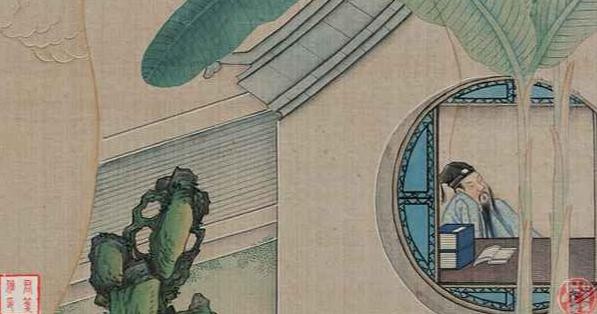
正如学者所指出的:"胡适的贡献在于建立了库恩(Thomas S. Kuhn)所说的新'典范'(paradigm)。而且这个'典范'约略具有库恩所说广狭两义:广义地说,它涉及了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entire constellation of beliefs, values and techniques)的改变;狭义方面,他的具体研究成果则起了'示范'(shared examples)的作用,即一方面开启了新的治学门径,而另一方面,又留下了许多待解决的新问题。"这一评价准确地概括了胡适在学术研究范式转型中的贡献。
《红楼梦考证》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对一部文学作品的研究,更在于它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学术研究方式。这种方式强调科学性、系统性和实证性,与传统学术研究中的主观臆断、内容零散、缺乏实证等特点形成鲜明对比。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王国维比胡适更早用现代学术研究方法、西方哲学思想来研究《红楼梦》,他的《红楼梦评论》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由于其理论基础是基于王国维个人性格与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契合,这种偶然的"个体性"契合无法提供一套可操作性的、适于推广的学术研究范式,也没有提出可供开拓的基本命题,因此《红楼梦评论》最终成为绝响,未能像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那样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为《红楼梦》这部古典小说在现代学术研究体制中的经典化做出了关键贡献。它不仅从研究观念、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为《红楼梦》研究提供了合法化的学理基础,也通过一套可操作的研究范式引导了后来的研究方向,促成了"新红学"的形成与发展。从学术史的角度看,《红楼梦考证》代表了中国学术研究范式的现代转型尝试,是中国学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参考资料
胡适:《红楼梦考证(初稿)》,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
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23年版
举报/反馈
网址:从《红楼梦考证》看胡适对中国学术研究范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 https://m.mxgxt.com/news/view/1806211
相关内容
张昊苏:对胡适《红楼梦》研究的反思 ——兼论当代红学的范式转换[上]卜喜逢:《红学史上的第一次学术碰撞——蔡胡论争考论》
《吴宓与胡适的〈红楼梦〉研究》出版
从多版本《红楼梦》看经典如何在传承中焕发新活力
《红楼梦》心理剖析,从心理学角度探索红楼人物
揭胡适对现代中国影响:他提供了观察世界方法
朱玉洁|胡抗美的现代书学探索
苗怀明整理:《蔡元培论红楼梦》
东塾红学三书:心系红楼,刘梦溪与《红楼梦》的不解之缘
卢飞宏:《中国大运河武术文化探索研究》引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