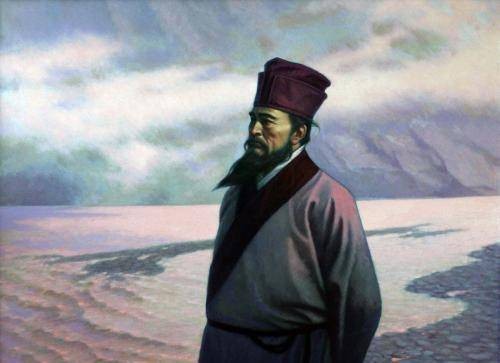1924年的中国文坛迎来了一位举世瞩目的贵客——印度诗圣泰戈尔。这位亚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梁启超、蔡元培等文化名流的盛情邀约下,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彼时的中国正处于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泰戈尔的到来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划过夜空,在知识界掀起巨大波澜。
泰戈尔便展现出惊人的文学天赋,8岁开始写诗,12岁就能创作剧本。他的代表作《飞鸟集》《新月集》等作品以其深邃的哲理和优美的诗性语言闻名于世。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更是在亚欧大陆掀起了一股经久不衰的泰戈尔热。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等进步人士积极引介泰戈尔的作品,其主张东方精神文明优于西方物质文明的思想,以及对中国的友好态度,都让他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赢得了广泛赞誉。 1924年4月12日,经过漫长的海上航行,泰戈尔乘坐热田丸号邮轮抵达上海码头,开启了他为期50天的中国之旅。这一文化盛事立即引发轰动,当时中国文坛的顶尖人物几乎倾巢而出:梁启超、蔡元培、梁漱溟、辜鸿铭、蒋梦麟、林长民等学界泰斗纷纷表达热烈欢迎。值得一提的是,曾留学剑桥的诗人徐志摩凭借其出色的英语能力担任泰戈尔的随行翻译。而林长民之女、新月社才女林徽因也因其欧洲游学经历和流利的英语,成为另一位重要翻译。 在徐志摩和林徽因的陪同下,泰戈尔先后访问了上海、杭州、南京、北京、济南等重要城市。在北京期间,京剧大师梅兰芳特意为泰戈尔献演《洛神》,泰戈尔还获邀拜访了暂居故宫的末代皇帝溥仪。所到之处,泰戈尔都受到无微不至的款待,以至于他动情地说:在中国,我没有丝毫的陌生之感。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对泰戈尔顶礼膜拜。在泰戈尔生日宴会上,当蔡元培等人为其举办隆重的祝寿会,林徽因和徐志摩还联袂出演泰戈尔名剧《齐德拉》,梁启超更赠予竺震旦这一中国名字时,性格耿直的鲁迅却愤然离席。在他看来,这种过分的崇洋媚外实在有失体统。不过细究其因,鲁迅的矛头更多是指向当时知识界的盲目崇拜风气,而非针对泰戈尔本人。 在长达一个多月的访问期间,徐志摩、林徽因与泰戈尔朝夕相处,三人被时人誉为苍松竹梅三友。这段亲密接触让徐志摩对林徽因的旧情复燃,他甚至恳请泰戈尔为其出谋划策。阅尽世事的泰戈尔自然洞悉这段微妙情愫,临别时特意创作《赠林》一诗相赠,以诗喻情,暗藏玄机。 徐志摩与林徽因的感情纠葛,恰如青春期的懵懂爱恋,炽热却难持久。当年为逃避包办婚姻,徐志摩狠心抛下襁褓中的幼子和发妻张幼仪,远赴剑桥求学。在那里,他邂逅了随父游历欧洲的林徽因。与传统的张幼仪相比,林徽因的才情与西学修养令徐志摩神魂颠倒。他不顾人伦,在张幼仪怀孕期间逼迫其堕胎,并在产后立即要求离婚。这种极端行为让18岁的林徽因清醒认识到:今日他能为你抛妻弃子,他日亦能为他人将你抛弃。1921年,林徽因毅然回国,在父亲安排下与梁启超之子梁思成订婚。 1924年泰戈尔访华,为徐志摩重续前缘提供了契机。泰戈尔倡导的平等自由思想深得新青年推崇,在陪同访问期间,徐志摩与林徽因不得不频繁接触。特别是在泰戈尔寿宴上,两人联袂出演《齐德拉》,徐志摩饰演爱神,林徽因扮演公主,剧中终成眷属的结局更让徐志摩想入非非。 泰戈尔以诗喻情,将三人关系比作天空、大地和微风:徐志摩如天空般浪漫不羁,林徽因似大地般清新可人,而梁思成则是那不可或缺的微风。正如林徽因晚年对女儿所言:徐志摩爱的不是真实的我,而是他想象中的诗人形象。这段感情注定无果,因为徐志摩追求的是爱情的幻象,而林徽因需要的是踏实的人生。不久后,徐志摩又陷入与陆小曼的婚外恋情,再次印证了他为爱痴狂的本性。而梁思成在新婚之夜那句为什么选择我的疑问,道出了这段感情中每个人内心的不安与彷徨。青春的爱恋就像迷雾中的森林,充满诱惑却也暗藏迷途。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