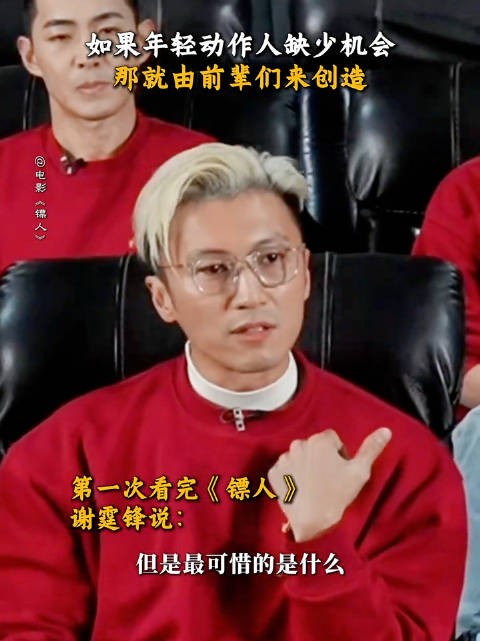踏着文学台阶寻求舞剧独有的审美境界

芭蕾舞剧《百合花》剧照 (摄影:张挺)
作家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经由上海芭蕾舞团改编,近日以舞剧形式与观众见面。青春叙事、唯美视像,让这一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沉淀的故事,闪耀出溪涧春水般的透亮光泽——
染坊外水青色的女子群舞,是引入故事的切口。舞蹈巧妙融入芭蕾足尖技巧,以江南特有的清新温婉,引领我们重拾记忆,参与到一场宏大的戏剧情感的布设中;
浴火而生的军人群像,历来是中国舞剧最具感染力的篇章。在《百合花》这部舞剧中,无论是流弹呼啸的清晨,还是战事逼近的血色黄昏,人民军队与百姓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情感载体、铺叙主干,而贯穿全剧的“步枪与山花”,则是编舞家以高度凝练的舞剧语言给出的题解——艺术的慧眼,穿透时空,落实于一个“崇高与浪漫”符号,精准而明晰;
全剧尾声的“百合花大群舞”,着意于芭蕾舞古典形式的回归。偌大篇幅中,洁白舞裙翩然如风,情感的流动江河般奔泻——用纯舞蹈展现人类共同的情感,用人性的光辉照亮跨语境交流的通道,是编舞家的终极追求,观众很理解、很认可,也很能够与之共情。
芭蕾舞剧《百合花》以戏剧情境讲述故事,以细腻手法描摹故事中的人——通讯员、小媳妇、大姐,有没有姓名不重要,他们之间所产生的人物关系、展现的人格魅力,构成了完整的戏剧性。通过这部见事、见人、见情感的当代剧作,我们也看到,三代文艺家对美学境界的追求,以及血脉传承和艺术个性对这部剧产生的深刻影响——
茹志鹃是经历过苏中战役的军队文艺工作者,这场被视为全国解放战争胜利起点的战斗,是小说《百合花》的特定背景。茹志鹃没有正面去描写战争,而是以女性作家的视角,以平实的笔触,书写战争年代人与人之间真挚淳朴的情感,通篇仿佛是一曲爱的牧歌,赞美崇高,仰望人性之美。时隔近70年,茹志鹃当年写作时采取的“创作来源于生活”“政治主题和人性审美完美结合”“通过平凡人物反映宏大历史背景”等手法,依然是今天文艺创作最有价值的经验。
年少时读《百合花》,我曾想,为什么在文笔清淡、五千来字的小说里,作者要花篇幅去写完全出于想象的通讯员“前史”:“我眼前出现了一片绿雾似的竹海,海中间,一条窄窄的石级山道,盘旋而上。一个肩膀宽宽的小伙,肩上垫了一块老蓝布,扛了几枝青竹,竹梢长长地拖在他后面”?为什么不按常规描写小通讯员灵活的身形、稚嫩的笑容,而反复提及这个未满20岁的战士“高挑挑的个子”“厚实实的肩膀”?为什么在描写他枪筒里“插了几根树枝”用于伪装后,用抒情笔调添上一笔:“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今日重读,我有种感悟:受到革命浪漫主义深刻影响的女作家,意在用含蓄深情的文字,塑造一个大众心目中的“美神”。在当时的年代,内心如果没有一种大的审美格局,不可能形成这样的追求。
这也是我十分敬佩的地方。古希腊人利用诗歌、绘画、雕像,创造了无数美神。历史以及与历史相关的文化,随着美神的故事流传,形成了“视美为生命力”的哲学观,它启发、影响着人类对美与爱的认知和实践,成为精神追求永恒的镜像。女作家则凭借一段不能忘却的记忆,热切向往创造一个从硝烟中站起来的“美神”。他淳朴刚毅的身姿以及青春笑颜,感动着每一个人,多少年后,依然是一个民族的青春偶像——多好的题材,故事单纯而寓意丰厚,特别适合舞剧去表现,而原作从方法、路径、情感、细节上提供了很好的指引。
王安忆受邀出任编剧,母女两代人形成跨时空情感链接——以现实主义为基底,表现普通人在历史洪流中的能动性,构建个体与时代互释的心灵世界,在这一点上,两代女作家的写作非常相近,相信在改编《百合花》时,默契程度也高。为芭蕾舞剧《百合花》撰写台本,在我看来,非王安忆莫属。事实上,从一开始王安忆就主张《百合花》要搬上舞台“必须加东西”。她以自身对芭蕾艺术的理解,认为“丰富性”是一个必要条件,其中包括心理层次的丰富以及想象力的进一步发散,而原作“太简单了”。
以小说家的理性思维,王安忆首先操作的是,为舞台行动寻求逻辑依据,这一点显得尤为必要。比如她为新媳妇的丈夫,也就是新郎,作了基本设定:他可以是参加主攻的战士,也可以是支前担架队的一员。这一点在原小说中并未提及,但王安忆认为,在舞剧中,这个新郎可以只在梦境中舞蹈,甚至可以不出场,但身份的“假设”一定要清晰准确,这关系到从新媳妇身上能生发多大的戏剧性。
除此之外,王安忆在台本中运用了大量的情境反差、色彩对比,乃至梦境、幻化,以增加舞剧的可视性和可感度,比如花轿与担架的幻变,激战前夜的月光与烽火的衔接……从视觉体验中寻求戏剧张力,本不是小说家的专长,但王安忆似乎对这部舞剧充满想象,且显得开阔而丰满,超越了她构架文学作品时的常规操作。
当然,最核心的还是对“百合花”这一主体意向的铺陈渲染——从染坊布匹“枣红底上呈现大朵大朵的百合花”“晨曦散去,只见一幅撒满百合花的被子展开在太阳底下”,到全剧最后一笔:“新媳妇展开她的新被子,轻轻覆盖通讯员。霎那间,遍地盛开百合花”,字里行间无不是与她母亲1958年那番写作情怀的呼应,并有新的发现与遐想。
如果,王安忆对舞剧的叙事能力、表意手段更多一点信任,我想,她会把这件事做得更深入。即便如此,在大多数舞剧台本还处在“写故事大纲”的今天,王安忆为接下来的编排,已经提供了足够多的开掘入口。仅新媳妇发现通讯员牺牲一节,她在台本中所作的提示:“茫然,怀疑,恍惚,终于确定,大恸。”就够编舞家好好琢磨——如何踏着文学的台阶,一步步去实现肢体语言精准而有效的表达。
王舸是我十分欣赏的当代编舞家。早先,一部《歌唱祖国》开了中国舞剧轻喜剧风格的先河,至今未曾淡忘。作为舞剧《百合花》总编导,王舸清楚,不能跪在文学脚下,而是要站在文学的肩膀上,寻求舞剧独有的审美境界。他从台本中看到了小说家对细节的严苛要求,也从中获得灵感。“借被子”这一关键情节,台本写道:“通讯员不由大喜,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放慢脚步,轻轻靠近,仿佛那被子是个活物,一有动静就长腿跑了。”这种由文字到舞台形象的转译是有难度的,但王舸深深领悟文学的微妙,用戏剧芭蕾手段,将“对白式”双人舞处理得丝丝入扣且充满情趣。
他不仅擅长细腻传神的人物刻画,在象征性表达和情绪的大色块铺陈上也独见功力。“母亲”这一形象是王舸宕开一笔的创造,虽然看似一个具体人物,本质上“母亲”是中国舞蹈诗学中最具典型意义的符号。母亲送出的军鞋以及满地撒落未及送出的军鞋,为观众理解人类深切的痛苦,提供了象征性框架。也许从风格上看它并不属于这部舞剧,但实际效果是好的,形成了强大的情感冲击。
全剧的结尾极为精彩,观众感悟到,当“美神”献出热血青春时,得到的不仅是圣洁的眼泪,更是纯净无瑕的爱——满地铺洒的百合花,寓意无限。
芭蕾舞剧《百合花》上演,让我们再次看到上海芭蕾舞团的创制实力。在以苏北民歌《拔根芦柴花》为素材的音乐旋律中,江南特色、年代氛围、民族意蕴、大剧气派得以充分展现。担任主演的几位青年芭蕾舞演员,大多是第一次独立创造角色,在导演启发下,很好发挥了技术优势和形象优势,塑造出生动鲜活、具有青春美感的人物形象,在如何表达中国式感情上,走过了一段从陌生到适应到富有创造的成长之路。
(作者方家骏,知名文艺评论家)
网址:踏着文学台阶寻求舞剧独有的审美境界 https://m.mxgxt.com/news/view/1608680
相关内容
寻根韶乐 :踏上歌舞剧创新征程打造有精神深度的舞剧审美样式
打造有精神深度的舞剧审美样式
时装秀挑战传统审美界限,引发文化与美学思考
融合戏曲、舞蹈、音乐剧 实验戏剧《四梦》寻求东方美学质感
戏剧舞台也要“节能减排”——中国环境网
独具一格的东方美学,爱与美的行者——美神煦氰闪耀世界舞台
二十年舞台经典回归 《我爱桃花》带来新中式审美
论中国当下影视审美所遭遇的国际性后语境哲学论文
游戏剧如何兼顾不同文化群体的审美需求